(編按:原文刊於明周文化2757期《香港文學 迷霧裏重行》。是次封面專題集結了黃碧雲、董啟章和淮遠三位重要的香港作家。他們的創作生涯,都見證着島與半島的跌宕。當中,黃碧雲並無選擇受訪,而是交來這篇逾六千字的長文,題作〈商場〉,以作品來作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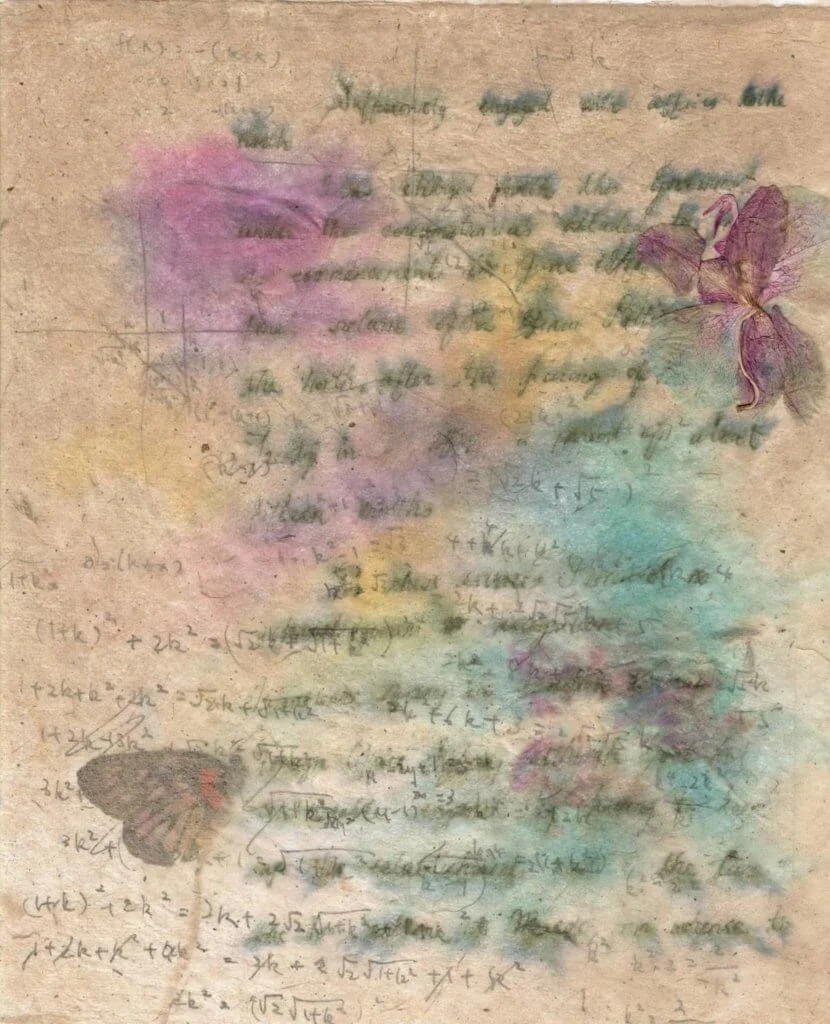
當人們離開,留下的會去商場。
商場,香港那麼獨特的,不是說別的地方沒有商場,但在他處,商場就是一個買嘢的地方,從貝魯特、曼谷、倫敦巴黎、紐約很久沒去過、大馬士革好像和使徒保羅前去時沒有兩樣是一個souk巿集但不是商場,souk很多玩很大很香都是阿拉伯香料微辣香、小伙子推着手推車、有糖果有珠寶有衣服有阿拉伯草藥但不是香港的商場那麼光潔明亮、星期五大馬士革巿場死寂香港是永不停止的城巿而Aleppo酒店在巿集裡面,走出去就是羶腥的羊肉氣味像活在一個屠殺之地,後來Aleppo為叛軍所佔領時常想那個巿集怎麼了、維也納住過了哲學的維根斯坦、寫小說的茨維格、作曲鋼琴家布拉姆斯、其作品作了無數商品的畫家Klimt講德語的城巿很華麗、我們現在還可以見到十九世紀的馬車及穿着黑西服拿手杖與長裙戴禮帽的一對年老夫婦以為是麗鬼、維也納的商場有舊建築物裡的gallery、或在新建築物裡賣貨的竟來自俄羅斯、捷克,但怎樣華麗都不是香港的商場、我無法記起俄羅斯聖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商場,不是沒有只是無法記憶,或者不盡愉快的緣故,只能記得我喜愛的杜妥托也夫斯基的房子與墳墓,見着他寫《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房子,所有的記憶只與佐西馬神父、和那個永在恐懼與永恆報復的殺人青年,與商場無關、而Irkurst西伯利亞不那麼冷日間零下三四度,商場無人為何商場不關也事實開些關些,雪地的遊樂場反而更多人站着滑雪梯,我買了一隻小鑽石14K金錶很高興但現在已經不戴錶不戴首飾、那種異地的物質快樂是不是在坐那一程夢想的橫西伯利亞火車除了在車上讀《靜靜的頓河》和不停的吃朱古力飲伏特加酒變成肥婆怪不得俄女老了都是大肥婆、原來你夢想的到了眼前變成肥、這樣我是否這樣知道夢想的本質、2019年香港情感大爆發、商場又成了聚集之地、但我從來沒有在爆發時進入商場、密封的地方好危險、我坐在商場對面的百步梯有人喊大家來這邊這裡有不反對通知書,如今想來真是天真、九龍灣德福花園,所有店都關了,所有人離開,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五時,平日一定好多人但那一天只有幾個護衛,和一兩個好心的阿姐,叫我,阿姐,前面有警察,不要去,這樣我留落在馬路,前面有一個精神病人,雙眼發亮,一邊走一邊言語,回望、他回望什麼,後面沒有人(我是人嗎),遠處天橋排了二三十架亮着紅藍燈的衝鋒車;走過了這麼遠我以為我很討厭香港及其商場,狹小、人多、嘈吵、貨品單一嚟嚟去去果幾間又貴,但我還是回頭商場,真是百年身。
商場還是商場,置地;一個離別的見面,她說,已經訂了在文華咖啡室,六時半,兩位。太久沒見我怕有冷場,多叫一個大家的共同朋友,她說,要不要改時間地點,我說,不用,這樣她還是工作效率的覆:三位,同樣時間地點。到了咖啡店,我說,我三十幾年沒有來過。我們還是做第一份工作時,不知怎的,會去文華喝一杯咖啡,時代記憶,文華沒有變,來侍的還是年輕乾淨,兩代人了吧,香港的古典,文華咖啡。另一個到,她說,乜嘢呀,咪同你嚟呢度排隊買過芝士餅?文華東方,殖民風情,英人眼中的精緻中國。(這樣我們就去了檳城的文華東方。有什麼好留戀的呢,外面那麼窮困污糟)。
噢,英國,Seven Oaks. 她跟我說過,我忘掉了。她有房子,不算是連根拔起。
幾年前去過Russell探我姊。她住四十幾年了。脫歐時才知,Russell是英格蘭最窮的幾個城巿之一。我們去Russell的泳池游泳,然後去商場,有我童年時穿過的其樂鞋店子,Clarks。我在Greggs買了一枝薑檸檬飲。姊姊很靜默,我看着她的背影,還是年輕女子的纖瘦,背有點僂;她的兒子前一兩年死了,我最後見他是他死前一年。我們去公園,他開一架紅色的二手保時捷,在一間血汗網購物流廠做。那間年輕的西班牙女子阿菲加流落在英國時做的,猛叫faster faster每夜十一時她開工的工廠,賺它十幾鎊一小時的人工,很好的了,比當侍應好。去公園的那一天,陽光很好,五月我們還要穿大衣,野地開滿血紅黑心的罌粟花,像野草,拔起就謝。姊姊轉過臉來,滿臉皺紋,不笑。還是戴着眼鏡。
文華酒店咖啡店,精緻安靜。原來這麼好。我差點說,原來有錢這麼好。
也不是沒有,一餐可以。但已經不欲。
年過六十,不過被遺棄就是我轉背。
然後我們找個地方喝一杯,游不喝酒,我會飲一杯啤酒。
這時才發覺,酒吧關十時,疫情時期,我已久久很少出門。
這時穿插無人的置地商場。每兩三個月,我會來這裡剪頭髮,但我剪完就走。
置地商場,香港八十年代最好的商場吧,在中環,有着那個時代物質競逐的得勝氣氛。太子商場,娛樂行太平行,怡和大廈以前叫康樂大廈,大家應該知道Jardines是東印度公司的商人,賣鴉片竟然在2019年⼜被炒熱,賦予新的意義,歷史真的有未來,不停注入。有人說要有東印度公司,但第一間東印度公司是荷蘭人的,去印尼取香料去賣,也是海盜與商人與軍人難分或結合的年代。在大鵬灣,疫情期間香港最遠去到蒲台島,北望是長洲,南向遠處的燈或日間似有似幻的土地是擔杆群島,即清《新安縣志》有記老萬山賊的海島,也是葡萄牙人所稱的「賊島」Ladrones Islands。香港海盜徐阿保的海盜團隊在大鵬灣被殲,英人記打死打落的海盜近千人,徐阿保逃脫。蒲台島有個廢棄古宅叫巫氏,這位商人記為因被海盜洗劫而離開,遺下古宅荒廢,當然最後勝利的是野草灌木,半山不長樹,和每季的蝴蝶。
中環的商場,我們記得當初的The Galleria, 會想起巴黎的Gallerie Vivienne,有蓋玻璃鐵拱屋頂通道小商場,舊巴黎的高傲眼,但香港的Galleria是你搵到錢就去玩冇錢都着靚靚去睇吓,那間名店門口有間叫Tiffany的花店,有個俄羅斯女子在賣花,每次走過都好香,像現在的IFC商場,曾經有過一個花店,不常去,不知是否還在。
但我們沒有走同樣的路。這置地商場,名字叫廣場,香港無情白事因為沒有所以乜都叫廣場,上水廣場,觀塘廣場,將軍澳不要忘記以前叫Junk Bay是堆填區即垃圾廣場,因為渴望Square或Plaza,其實Square或Plaza都是空地,但在香港就是商場。置地廣場,我們開始的地方,然後各自各,離開的人她很會走中環廣場的道路,而我,不知何方,還是站在原地,老了快四十年。
這一夜我們分別。一九九七年之前的劇目,再演一次。
我們是否已經熟練。香港人的來來去去。1841年英人佔領了香港但沒有正式條約,炮船邊上中國炮轟從舟山群島入寧波、上海、乍浦、鎮江至南京長江之外,找個年輕的莊士頓在香港看着建港督府,開路,莊士頓寫回倫敦的公文信部份留在倫敦國家檔案處,部份留在香港。手寫字紙又發黃看不清楚,香港是⋯⋯Hee ??? Port.猜了好久原來看檔案最吃力是看手寫字,那是現在少見的鋼筆字大寫F,⋯⋯香港是Free Port. 為什麼要寫大草?一個地方的專有稱呼而不是泛稱,仍然是嗎,free port。但你怎樣理解它,free port。自由港。貨物自由,人自由,他們都離開,又另一班人進駐,政治上呢,或我寫?或我想?我怎樣說大嶼山就是監獄島呢,監獄爆棚的香港。Free port,免稅城巿,間諜城巿,予取予携,政權轉換。
Free Port並不是清道光年江寧布政使黃恩彤記載的「香港本海中荒島,在急水門(現稱汲水門)外,地屬新安,距離縣城一百餘里,有蛋戶十餘家,傍岸寄居,捕魚餬口,近日英人據為己居,實非香港,仍全島東偏瀕海之裙帶路也〔嘩噢,原來英人所據不是香港是裙帶路佢都算狼死〕〔黃恩彤是英軍口中的「明日之星」〕〔是年三十八,從二品官,頂戴起花珊瑚,穿九蟒五爪朝服〕。⋯⋯其地初經開闢,房屋無多,洋樓尤少,較諸澳門相去遠矣。有二炮台,俱在平地,開一直路約二十餘里,可以馳馬行車。」黃恩彤於1843年6月、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簽訂後的九個月來過香港,寫給四等侍衛咸齡的信:「我兩人株守無益,不如逕赴香港,示以不疑」〔之前又話唔係香港係裙帶路?〕。黃恩彤、咸齡,耆英,伊里布,牛鑒,五人上英炮船簽約,後三者鈐印在條約的影印本見到。

我沒有去過西九龍中心,一路之隔,會望着。旁邊有長沙灣政府合署。西九龍中心,哎,商場的另一個喜稱,都是香港沒有的:中心。那麼多中心,但我們知道,中心的字義只是一個範圍之中的唯一。後來才知道,那是隔了幾代人喜歡去的地方,我在路的對面,鴨寮街尾的一條巷仔。深水埗的巷仔,或者是因為有我熟悉的舊香港,日光日白,鴨寮街的老鼠好大隻又好大膽,在擠滿人的叫街像廟街到底是不是街只是露天貨場,老鼠急竄醒目的檔主立即踢足球一樣將老鼠踢高但我們知老鼠與人類並存被人類打壓趕絕竟不絕還隨時反擊,落地老鼠依然矯健的逃跑跑到我腳面來,人類也不壞比老鼠也是反應快求存,我不知時已經彈起了老鼠沒有爬經我,牠消失了鴨寮街人又在叫賣客人問這問那。巷仔沒名字,有兩間錶鋪,一間賣MD 〔已停產的一種播音樂或錄音的器材〕企圖留住時間的人會來買,一間只寫了電話號碼的理髮「店」,你要剪髮就call佢,像什麼皇室理髮師,幾十皮剪個髮,她有其他工作做,巷仔同人說。
巷仔流連了一班人,都老。不是美沙酮友,不是賭棋老,不是塞廿皮當食雞的公園聽歌老哥哥,老也有很多不同方式,他們不會去西九龍中心。或者不會過那條馬路。那一條馬路,隔了兩個世代,香港的三十年。
2019年的狂喜,因為它打破了路的隔離。西九龍中心門前站滿防暴警察。所有檔口都關了,巷仔無人。鴨寮街出現了可能平日在西九龍中心出現的人。那天是星期六。有個人走上前來,跟我說,EE,你不要留在這裡,好危險。
這樣從西九龍中心一直走到長沙灣。日光日白,人很少。
我見到那一個我嗎,住在新城巿廣場樓上的那一個,對人生充滿失望與疑惑,每一天都覺得地獄之火,將我燃燒。
我怎樣記憶,她失望頂透的時候,堅決離開一個她以為曾經答應,但她看着行業裡每一張發青的臉孔,每周開會的時候她看着同隊的人,那一年她二十八歲,畀人叫阿姐,到今日今時,阿姐做了幾十年,都算永恆。那些臉孔:她在死前的長兄見到,如同猴子在火場無法逃離的焦慮驚恐又盡其所能,她想:我要離開。然後她搬到新城巿廣場樓上,換了一份工作,返九點。她第一份返九點的工作,晚上去打機打到機鋪關門兩點,睡幾小時洗個臉,到公司喝三杯咖啡,每小時去廁所洗把臉,在公司寫自己稿,無賴但痛苦的捱着,六個月便走了。
在百利商場開一間小店。小商場真好玩,結果又是肥。小商場平日沒甚生意,很少人行,無聊時每店都在叫外賣,全場最好生意是那間茶餐廳外賣店,吃完又吃,愈沒生意便愈肥。
賺到錢便到同場樓下去買他們從歐洲買回來的二手皮衣手畫牛仔褲,結果又是零雞蛋兼貼錢。
又肥又冇錢,必然結果:商場不可褻玩。不要輕看生意人的付出。
愛到最後是炒車。後來好少去商場。
新城巿廣場,早上六時,年初一,她在和一個死纏爛打的編導,傾橋傾到這一年開始的早晨,無家的人,她送她到新城巿廣場外面的公路,清晨的小巴正如香港最爛鬥的,忠誠的將所有離散在照顧之外的人載走。
可不知紅van有無在年初一早上六時的行走起價。
新城巿廣場的報攤,壹周刊報導是全港最賺錢的報攤,她很快的放下錢拿走報紙,賣報的人像馬戲團的千手人,她訝異手揚的速度,如舞。巿井藝術,香港她以為最好的品質,是不自覺,庸俗,卑下,無知識,吵,急,快,到。
那麼令人氣餒,香港不是紐約倫敦巴黎,老了她站在路邊看小伙子搬貨,那麼準確,不比芭蕾的拋接更少的力度與鍛練,而無人鍾愛。
肥仔很鍾愛的八佰伴,她已經離開,他還是個中學生;他喜歡的是日本咖哩,鍾情至多年後依然纏綿,而她只是匆匆的,在八佰伴關門之前,買一隻椰青,穿過那時還很少人的長廊,只有她一個,鞋子咯咯的廻響,她向前無路,向後無人,走回小小的租住的小房子。從來未見過業主的小房子,她數過,從房子的一端到另一端,七步。她以為會發瘋。
後來知道,期數的小房間。兩個囚友,一個持械行劫,一個販毒,大家一起釘書:「佢哋講出面去邊度食邊度玩。」一個在群眾之中可以不停講三小時的人,在這麼的一個房間,特別期數,靜默。
新城巿廣場穿過去,沙田街巿,更老的禾輋、瀝源,都有屋邨商場,商場有新城巿沒有五金鋪,海味鋪。對面是沙田警署,她入過去,不是被捕人而是受害人。但她不以為害,也不#MeToo,因為最強的是不以為害,也不與⼈metoo,我為什麼要和你一樣,自憐自傷。為什麼乜都群一餐。對面是泳池,離開了那個烈火學園她就去沙田泳池游泳,冬天有暖水。
壹周刊什麼時候消失,她都忘記。音樂噴泉消失。報紙檔也很久很久沒了。
死的死,她寫的都是夕陽字。報紙是夕陽行業,她有點倖災樂禍,好呀,沒了報紙你們就看人人都是記者充權時代的自媒、自己關自己把好唔得閒。
永恆在裝修的UA戲院,一個無人下午她去看了黃真真的一部六樓後座。戲院只有幾個人。
黃真真?邊個?定泰國菜黃珍珍?
她過去了,新城巿廣場還亮麗的變身,好多拖喼她都不敢去。
不敢去已經在她的商場年代終結之後很多年。
Agnés B那間咖啡店,約人見面,原來關了。粉紅化妝店還在但已經沒有人。那幾級樓梯大概博大陸人跌死不敢告她。City’super好貴但有她喜愛的黑豆餅,還有老牌瑪莎;她的路標還是以店鋪計,雖然知道,店會關人會走。Kérastase還在嗎賣頭髮用品都可以這麼高檔,日本見到Enoteca才知道香港都有,賣酒。Uniqlo長做長做,人們為什麼需要那麼多衣服,以為衣服是食物。化妝手袋店悄悄退場,體育家居,成了疫情的新熱。
總是有生命,商場如山頭野草,見着榮枯,不是一榮一枯,而是枯草夾着嫩新熟綠。顏色一定雜。
星期日的新城巿廣場,很多人,東鐵以前叫火車的站外有年輕男女在busking,唱Cantonpop,不知他們叫什麼,我還是很九十年代,那些很喜愛香港暫留的英語系國家人叫的Cantonpop,那不肯讓地的圍村祠堂望着上去商場的人,自己就變賣涼果小鋪,飛髮鋪,巴士總是有秩序的長龍,我們經歷了什麼嗎,我們願意記着或忘記什麼嗎,不由你。
這樣來了奧運。人們又再去到商場,又再一次歡呼,香港人。那麼微,但我們就是小地小人,點拼啊,一個金牌全城欣喜若狂,而欣喜之地,呼喚之地,翻轉與重回之地,都是商場,所以叫廣場,Square或Plaza,中心。
A Free Port。好多人讀書,好多人有偉大理想,然後。商場加高了鐵欄,行人欄杆的八角螺絲加了螺絲套,行人天橋更像動物園了,直行的動物。其他,只要你留在商場,或各線鐵路,直行走路,真的沒什麼。
他說,你常說沒什麼。我只好答,那是個對生命及對自己都失望頂透的人壓抑着,走路時頭時常要揚起,眼睛平視。她去見一個年輕女子,她也要離開,其實她不認識她,她無所謂,手機不加密,寫什麼全名全姓全地址,要拉你要斬你,不至歡迎但不意外。年輕女子說,其實我有一點內疚。
她沒說什麼。各安其疚,或咎。
其實我真想到商場去看一場比賽,什麼也好,什麼人也去,然後一起,歡呼拍掌。
她記得很多很多年前,她哥哥的孩子還小,他們去看煙花。尖沙嘴很多人,他們在商場大廈之外,開始擠,過天橋。
疫情時期,他和她見面、那一天他十分煩燥,扯下口罩抽煙。有好些人停下看他。她沒有叫他戴回口罩。他買了一罐啤酒,沒有買給她,也沒有問她要不要,不像平日的他。她默默的答應着他,很早,她說,我走了。她知道他會繼續去飲,他會每一夜都喝醉,喝醉了也跟平日沒兩樣,說話慢一點。她很少,一到即止,不喝。
最後一天她給他的短訊,「咦原來昨天月圓但下雨看不見」,他答「今晚應見到了」。
正如他讀過的,他和她都知道,沒有事情是未發生過的,不過來到眼前,她還是有點呆;他們來拘捕他的時候,早上六時。
商場還沒有開門的時候,曾經火燒。
PROFILE
香港作家,1961年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亦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犯罪學碩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學專業証書,合格執業律師。現修讀香港大學持續專業進修地球科學系應用地球科學碩士課程。曾任香港英文虎報記者、議員助理、開過服飾店等。屢獲港台兩地各大文學獎。著作有《烈女圖》、《後殖民誌》、《沉默。暗啞。微小。》、《末日酒店》(中英文對)、《烈佬傳》、《微喜重行》和《盧麒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