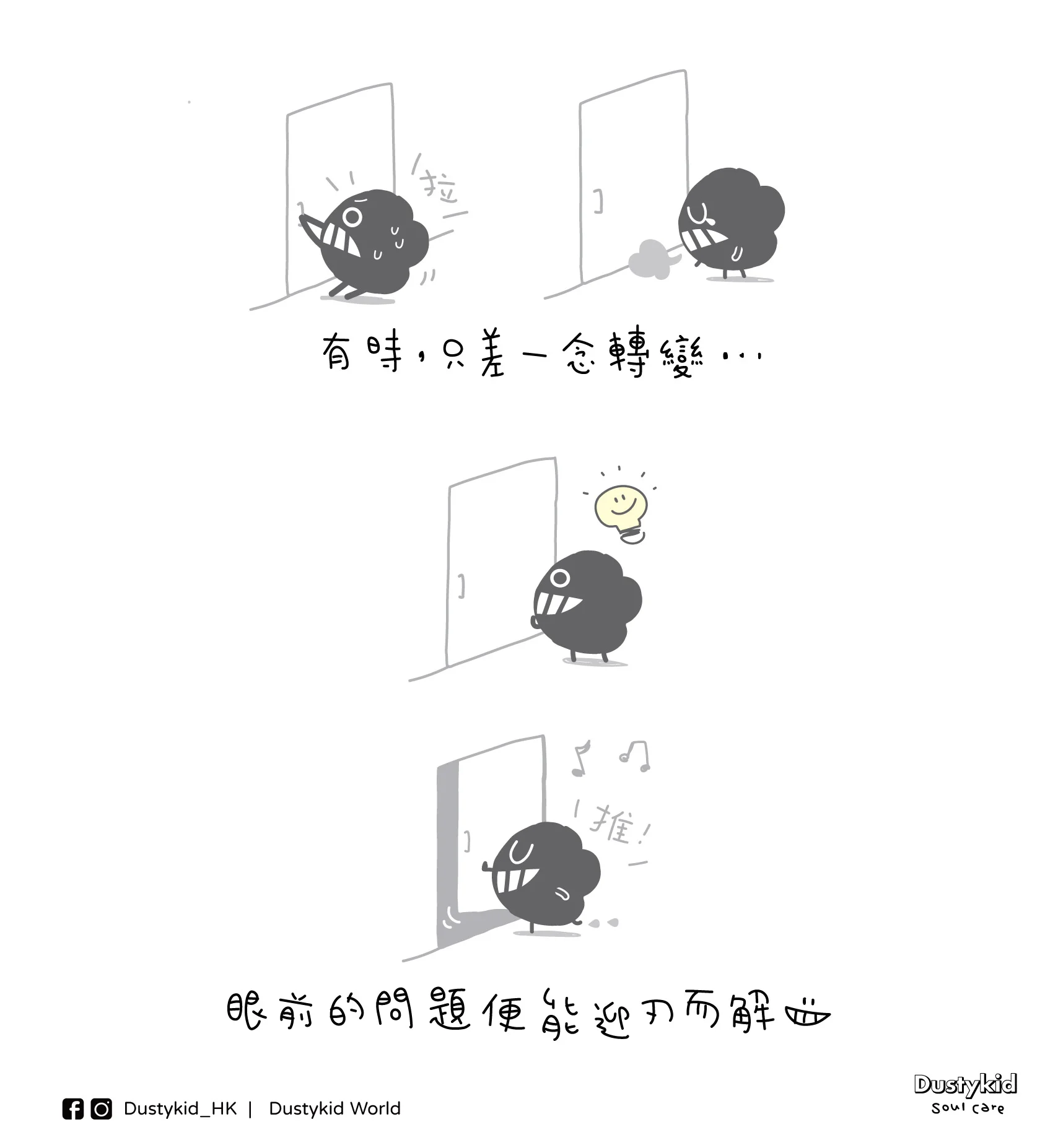《後人間喜劇》這本書的故事,是二〇一八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駐校作家的時候開始醞釀的。從八月初到十二月底,我住在大學校園裏的南大湖畔。南大湖背後有一段美談—話說五十年代南洋大學(南洋理大的前身)創校之初,資金匱乏,為了建設校園,師生們胼手胝足,合力挖出了一個大湖。自此南大湖便成為了南大的名勝。環湖小路叫做南洋谷,沿路立着一排白色的舊式小樓房,用作教員宿舍。我住在其中一幢樓房的三樓,窗外就是湖景—如果湖還在的話。
也許是小小的不幸,我駐校期間南大湖正在進行重整工程,計劃是改建為一個漂亮的公園。公園內依然會有湖,但形態和大小應該和原本的不同。我最初看到的,是一個巨大的泥坑,挖泥車每天在重塑坑的深度和形狀。在接着的半年,我目睹新的湖漸漸成形,湖畔架起了各種建構物的雛形,看樣子相信是未來的瀑布、引水道、觀賞台、小路等等設施。我未及看到新公園的落成,駐校期便結束了。
雖然施工有點吵,但我天天站在窗前觀看工程進展,也有點樂在其中。有一天我忽發奇想,覺得工人正在湖底挖掘一條秘密隧道。這條隧道將會通往附近的軍事設施。在發生什麼緊急事故的時候,特種部隊會通過秘密隧道,從湖中悄悄鑽出來,執行特別任務。一年後,這個古怪的念頭成為了我的新小說裏的一個情節。
如果說《後人間喜劇》的構思就是從這條想像的湖底隧道中冒出來的,可能會太誇張。不過,小說的大部分靈感,的確是在駐校期間產生的。初到南大的時候,一個人住在宿舍,人生路不熟,大學位置又頗為偏遠,整天困在校園裏。晚上打開電視,發現有一個韓劇頻道,便即管看看,怎料一看便放不下來。我之前從來不看韓劇,但在南大卻看了好幾部,有些也不算是特別吸引的,只是像服食了催眠藥似的產生了依賴。
其中有一齣《鄰家律師趙德浩》,講大有前途的檢察官趙德浩,因為正義感太強,處事手法也太大膽,而觸怒了惡勢力。他被壞人設局丟了官,前途盡毀,妻子帶着女兒離去,一度陷入人生低谷,甚至淪為流浪漢(很韓劇的煽情橋段)。後來奮發圖強當回律師,為弱勢者尋求公義,對抗惡勢力,因此而跟舊人仇敵再次碰頭,鬥得你死我活。雖然情節甚為精采,但也不過是常見的通俗故事。
後來我在宿舍裏苦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頭腦中冒出了按照康德的先驗論,打造一台「康德機器」(Kant Machine)的可能性。一部科幻小說的雛形便在我的腦海中出現。只是,這個概念如何化為故事,需要什麼人物,開頭還是毫無頭緒。大概到了駐校的中段,有一天我的思緒中出現「胡德浩」這個名字。很明顯,「胡德浩」是從《鄰家律師趙德浩》那裏來的,但胡德浩不是律師,他是個科學家。他是哪方面的科學家?當然是模控學,cybernetics啦!
我也是在駐校時期開始閱讀關於模控學的書,特別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和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的理論。當然還有討論模控學和「後人類」的路標之作,文學評論家Katherine Hayles的《How We Became Posthuman》。這些我從前在這個專欄裏都曾經寫過。事情就這樣一拍即合。有了科幻部分的概念,又有了故事部分的人物,一部新小說的胎兒慢慢成形,但距離它的出生,還需要孕育一段日子。當時的要務,是好好讀完康德的三大批判。這個任務,我一直進行到次年年中,即是回港之後半年了。
二〇一九年六月,香港爆發了反送中運動,社會形勢急劇惡化。思維的衝擊和情緒的波動,令許多人在這段日子無法專心做事。我準備好開筆的小說也一拖再拖。受到韓劇啟發的故事,是一部通俗喜劇,跟當前的氣氛格格不入。在這個被現實的陰霾全面籠罩的時刻,絕無可能把故事設定在香港。其實我早就決定把主要場景設定在新加坡,但對於香港的部分卻舉棋不定。且別說兩個城市歷來常常被拿來比較,在當時的局勢下,一個變成了人間地獄,另一個則依然是人間天堂。(至少從舒適和安穩的角度而言。)我決定把兩邊寫成平行世界,而主角胡德浩從一邊跑到另一邊,經歷了如夢似幻的人生。
這是我第一次寫主要場景不是香港的小說,也是第一次全面動用了通俗小說的形式。包括胡德浩在內的所有主要人物,無論外形、性格和名稱也是取自《鄰家律師趙德浩》的。妻子張海卿變成社會菁英柳海清,年輕女律師李恩祖變成女學生林恩祖,地方檢察院檢察長申瑛溢變成國家科技委員會主席江英逸,律師事務所總裁張信祐(張海卿父親)變成了前內閣部長柳信祐,壞蛋企業家鄭金茂變成同樣是壞蛋企業家的周金茂,還有申瑛溢的檢察官兒子申志旭變成了機器人學年輕學者江志旭……情況就好像我請了那批演員去演一部人物設定相似,但題材卻完全不同的戲。
這部小說由去年十月中開筆,到十二月底完成,共二十四萬字,只是用了七十多天。這個速度,除了是因為情節緊湊的使然,也反映了我內心的某種迫急。不是急於求成,而是在急轉直下的現實情勢下,作出的一個徒勞的力挽狂瀾的姿態。當然,所謂的力挽狂瀾,不過是純屬妄想。一本小說不能挽回什麼。它只能用狂想實現自己的自由,以及用笑聲,去抵禦現實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