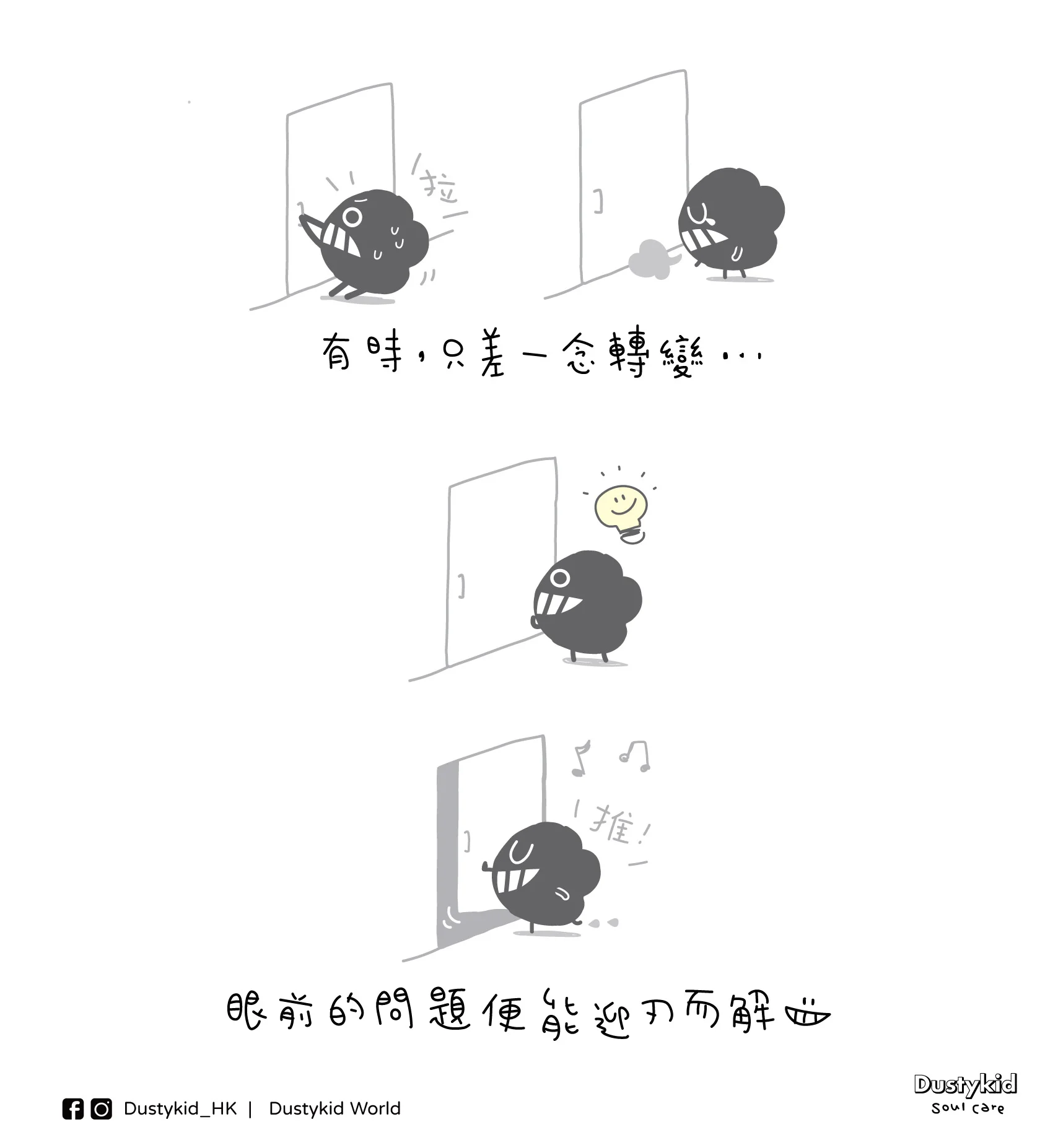那個屋子有個院子,院裏種了一株桑樹,除了這桑樹根下一圈裸露着土,這小小的前院地面皆被水泥蓋住了。但因那裂縫處處的水泥或年代久遠了,竟有一種說不出的被主人或來往訪客(想是不多)的鞋踩磨的刨光油潤感。我的母親在這間三層樓但窄小的日式房子裏過世了。但事實上,夢中這個屋子,在現實裏是我永和老家那院落較它大許多。同樣也是半世紀以上的日式老屋的隔壁。即使我父親過世這麼多年,我們家院子裏,從前父親親手種下的芒果樹、桂圓樹、白梅、木蘭、杜鵑叢,都高大蓊鬱,樹蔭隔牆蓋過這鄰居的屋子。
這條弄子裏,原本都是像我們家一樣的魚鱗黑瓦日本宿舍吧。不同年代,各自兩戶併一起讓地產商建起大樓,有六七樓的,如今老舊醜陋不堪,也有弄子那側三戶合併成一基地,這幾年才蓋起一十幾層的新大樓。在那像時光地質礦脈的靜巷裏,就剩下我家,和隔壁這間,是唯一不變,牆上淹流着藤葉或小紫花或整片青苔的灰綠色,貓在那陰影和光照間自在慢走,鳥雀盤桓、粉蝶飛舞,而屋子本身也禁錮着一種像舊水缸裏的貯水,那樣的陰涼。
但在那個夢裏,我母親為何不是在我們原來的那老屋的臥榻,嚥下最後一口氣;而是在隔壁的這窄小許多的屋子?也因之在夢中,我第一次進入那從小只是「隔壁」的那狹小的,其實像是一個電影裏演的,監視某個地下叛亂組織的特務,暫時租下,隱藏其中的小房子。這個房子沒有曾經生活其中的氣味,比較像警衞、門傭、司機的宿舍。一種伶仃、邊緣者暫時窩一下的,空洞無感性的畸零地。它其實已改建過了,日式老屋的魚鱗黑瓦已拆,朝上增高為一三層樓的小獨立樓。但各層的坪數非常小,且還堅持那四、五十年前台北樓屋,各層樓前必要開一扇木框窗,外頭有一口袋般的細磨石小陽台。我在夢中感受着自己的皮鞋底,刷刷踩過那小院外的粉塵,踩進門檻、那屋內的下面彷彿空心的木地板,從非常窄的磨石小樓梯上到二樓。我姊姊、我哥,還有我母親唯一的妹妹,都在那小房間,圍着閉着眼躺着的我母親,低聲討論一些什麼。
而這樣站在這像穀倉閣樓的小房間裏,雖然窄仄,但因四面都開窗,陽光像白粉一樣明亮的灑進來。甚至可感到因貼近隔壁(也就是真實裏的我家)的高大樹木,不同形廓的葉片像海浪翻湧,那樣無聲水流般的綠光在這應該是悲傷的空間,天花板、牆壁、榻榻米、五斗櫃……,一種我們在一艘隨波搖晃的小船船艙裏的印象。
夢中我姊姊穿一身黑洋裝,轉過身來,低聲對站在像一個傀偶戲小舞台景框外的我,說着母親過世前這一天,發生的一切。她的情感低抑而哀傷,以至描述那個在躺下如我們眼前死者之前,母親在這小屋內上下拿東西走動的細節,像在描述一隻上發條的機械玩偶。一些沒有關鍵線索的「生活起居注」。事實上,那不只是母親死前幾個小時內的活動,而是我們遺忘了的,這十年來,她在這屋內,一直重複的,無奇的,無論你將之分解、慢速播放,或是連續成無聲電影的走上樓、走下樓、發呆,拿出櫥櫃裏一塊祭神的糕餅,一口一口咀嚼着,打電話、拿鋁盆開窗澆水那些小陽台上的鐵線蕨、跳舞蘭、小銀杏盆栽……,都沒有足以形成「事件」的線索。
但我旋即發現姊姊這樣的憂悒,後頭有一種對母親死後,自己處境的不安。似乎母親生前已作好處置:隔壁那幢(真實世界我父親留下許多大樹的老屋)留給我哥,而夢中這幢小屋留給我。作為女兒的姊姊,除了一些紀念性的貼身首飾,什麼也沒有。在夢中我告訴那不熟悉的姊姊:不用擔心,妳就留在這住下去。但夢中我腦海也浮現出淡淡疑惑,這麼窄小的屋子,難道之後的時光,我要和姊姊共居於此,像對夫妻那樣一起生活,同榻而眠?
這時,這個屋子在夢中變大了。不,不是變大,而是像鐵路局替一輛列車加掛車廂,同樣那般狹小的空間感,但房間從門出去,又增殖出一樣那麼窄的其他房間。而每個房間裏,都像醫院長廊候診椅那般,坐着一排臉孔悲戚、衣服暗色的親戚們,他們都是來哀悼我母親的死去。但我並不認識他們。
我姊姊這時低聲對我說:我們的父親(他已過世十幾年了)也來了,就坐在其中一個房間那一排人羣裏。我順着目光看去,父親確實呈現成一個光霧,也許那是亡者靈魂的投影解析極限了。我姊暗示我,我們要裝作沒發現他也來了。免得他因害羞而又遁走。或他不喜歡讓人們覺得他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