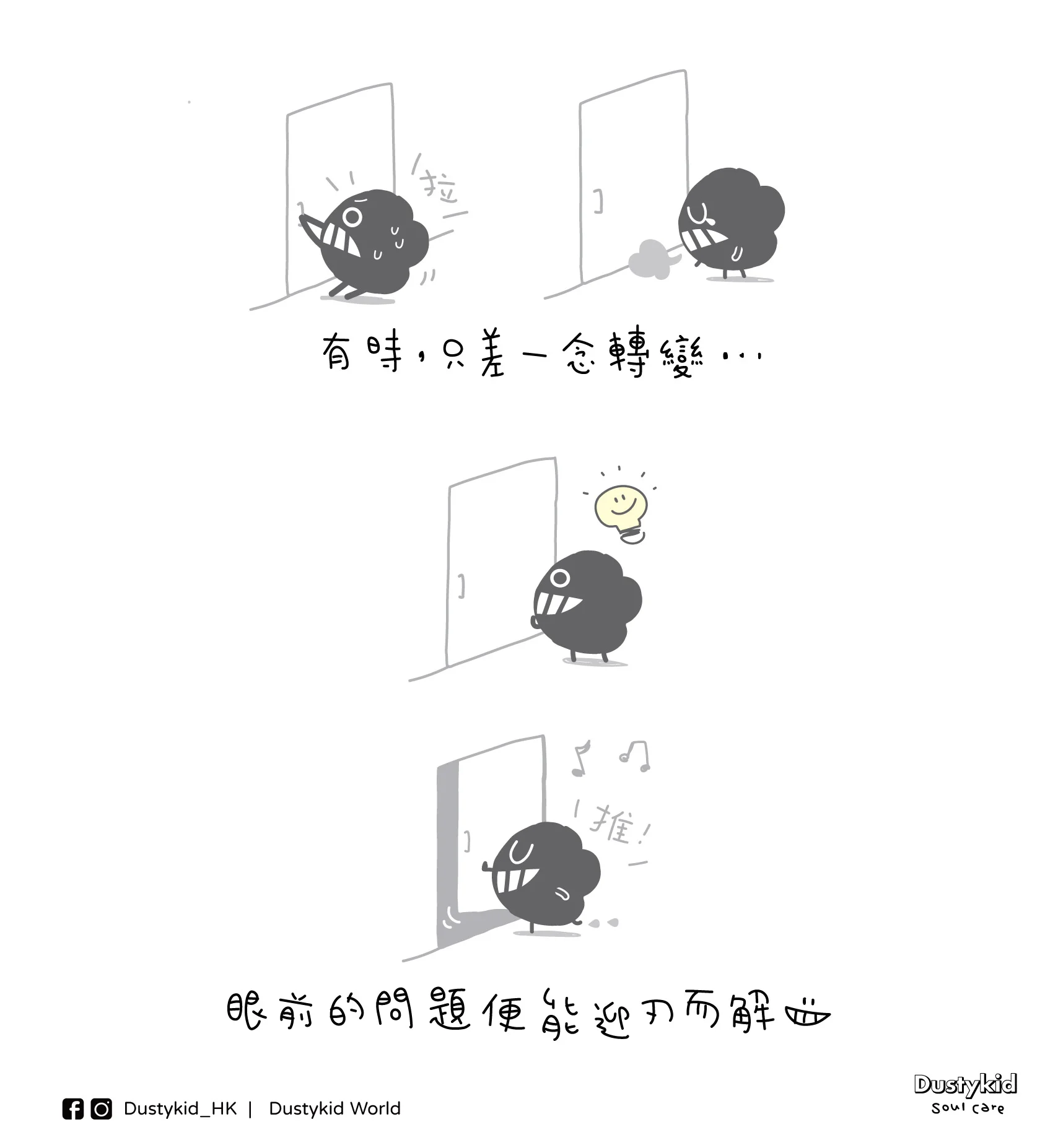但這種憂慮的情緒沒有連續劇式的爆發,而被另一種憂慮取代。我站在佛堂(其實低簷窄仄的小間過道),母親的臉似笑非笑,告訴我,他知道了妻名下買了一幢台北市的小套房,天啊,那一個月要繳五、六萬的房貸吧?這件事是妻最好的同事安娜告訴我母親的,夢中如水銀墜地,細微的線索連結,原來安娜是我阿姨的乾女兒之類的,在她們另闢出來的人際聚會中,安娜不知我們瞞着母親在外有房子這件事,純粹只是擔憂好姐妹被房貸壓的喘不過氣,殊不知,我母親現今仍在她那老人微薄的退休金裏,每月提撥兩萬元支援我們,他相信我這樣沒工作,可憐的媳婦扛着這個小家庭,小孩教育費什麼的。結果他自己省吃儉用,我們是老鼠咬米袋,偷偷在外頭(而且是用妻的名字)買了個那麼超現實的房子!
母親帶着笑說:「我知道心裏很開心,之後總算不用每個月操心兩萬塊了。」
夢中的我,則像小時候犯了什麼錯,抵死裝傻,把臉變成年糕那樣灰灰無表情:「他買房子,咦,我不知道這件事啊……」
我哥則在一旁咪着貓臉笑,確實他太開心了吧,惘惘有一種打迷糊仗的未來現實:有一天父親走了(現實中他老人家早已走了),母親她走了,這種老屋的產權,究竟是要我們三個老兄妹分?還是直接過戶給我父母最疼愛的那個孩子(我哥我姐都沒結婚)?如今你們這房在外頭已經自個兒買房了,那似乎局勢嘩啦就解了。
夢中的我或是太擔心了,非常輕鬆,像摘菱角那樣從嘴巴,被無痛的掰下兩顆連在一起的牙齒,母親、我哥、我一起湊進觀察那落齒,討論着:「這沒得救了,裝不回去了,你看,其實它們已是之前在牙根上裝過的假齒,現在剝落了,就像乾癟掉落的豆莢,掉多少剩多少,是大自然的法則。」
後來我又要踅回那父親的臥房,想是安撫一下孩子,但(當然)孩子已不生我的氣了,事實上他在這段時間又長大了幾歲,一旁是他的弟弟(何時冒出來的?),兩兄弟各自盯着面前的一台筆電,弟弟可能再看類似《豆豆先生》或《膽小狗英雄》那樣無厘頭的卡通,所以一直呵呵呵的笑。變成已是個哥哥的孩子,頭上戴着耳機,可能在觀賞某個「美國達人秀」的美聲演唱吧?難怪兩兄弟兩台電腦如此靠近,兩小孩都盤坐在祖父的大牀上,各自熒幕湧出的聲光宇宙,卻不會干擾到對方。我拍拍孩子,他拿下耳機,黑白分明的大眼望着我,線條柔和,完全不記得之前被我用吊衣架抽打的事啦。我用手語跟他比一比(不知為何,我們像電影裏的海豹特戰部隊,要攻堅一處敵人建築物前,在掩體後方比着手勢暗號,其實可以直接用講的嘛),他心領神會的點頭,可能細微的無聲溝通是:「媽媽回來就不能玩電腦嘍。」孩子乖馴的點頭。
這時我想,我總是要解決,「妻不知道母親因已經知道她在外面買房子」,或是要找到藤蔓觸鬚,像我小時候撒了謊總要想到「把現實曲拗成跟我說的那個謊一樣的形狀」,所謂「反向圓謊」。我必須在妻回家,猝不及防與母親遭遇,對質之前,找到那個關鍵人物安娜,從她那裏動手腳。或許讓她不經意打個電話給母親:「伯母,對不起,我那天弄錯了,我記成的是另一個人。」或若是這安娜,是個正直固執的人,我若能啟動其他支援系統,向母親證明,這女的有妄想症,說謊症,精神病院病史。
但我卻在這老屋通向「外頭」(可能是一條我從小便熟之不能再熟的小馬路;但也很像是地下捷運站出口,爬了像神廟那麼陡窄的階梯,終於迎着強光,會走到「地面上的世界」)的某處是遮雨篷蓋住的防火巷,或是一間後間疊牀架屋,另增蓋了迷宮般的後來的神祇的分廳,穿梭之間的鼠道──和兩個哥們,倚牆蹺腳,抽着有大麻氣味的捲菸,頹廢的哈拉着。哈拉着什麼呢?我們三個的臉,都像煎鍋廢油上方滾浪空氣變形、模糊、流動的臉。
我說:「……我想AI現在的新奇和無限想像,還在生產和如何生產,以及如同工業革命後的人類社會階級之重組,和新的倫理。但我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不是汽車,電腦,原子彈,電影,而是小說。兩位可能不為然小說不是幾百年前就有了?但細覽其結構、排列次元,整個歐洲整列天才,拉美,美國,印度,非洲,日本,俄國,小說在二十世紀累積的是,人類大腦最奢侈的那一整鍋只用小咖啡匙撈一杓的行為,穿過整個二十世紀,他不是人均GDP,現在想像AI的大運算『可能超越人腦』,用的就是『人腦平均GDP』,不,可能只有當時被懷疑是外星人愛因斯坦和海森堡那些發明量子力學的黃金腦袋,可以一比,想想杜氏加卡夫卡加福婁拜加納博可夫加波赫士加馬奎斯加奈波爾卡爾維諾魯西迪加普魯斯特……它在離開二十世紀後,長出的不是有沒有超越,而是如何變簡單,可變,傻逼,可以人人讀懂,賣得好。我感覺現在說AI記憶力強,都只是一種線狀或是面狀的想像,但別輕視了二十世紀人類中,所謂上帝已死之後,一些天才曾經趨近去觸摸『靈魂這件事』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