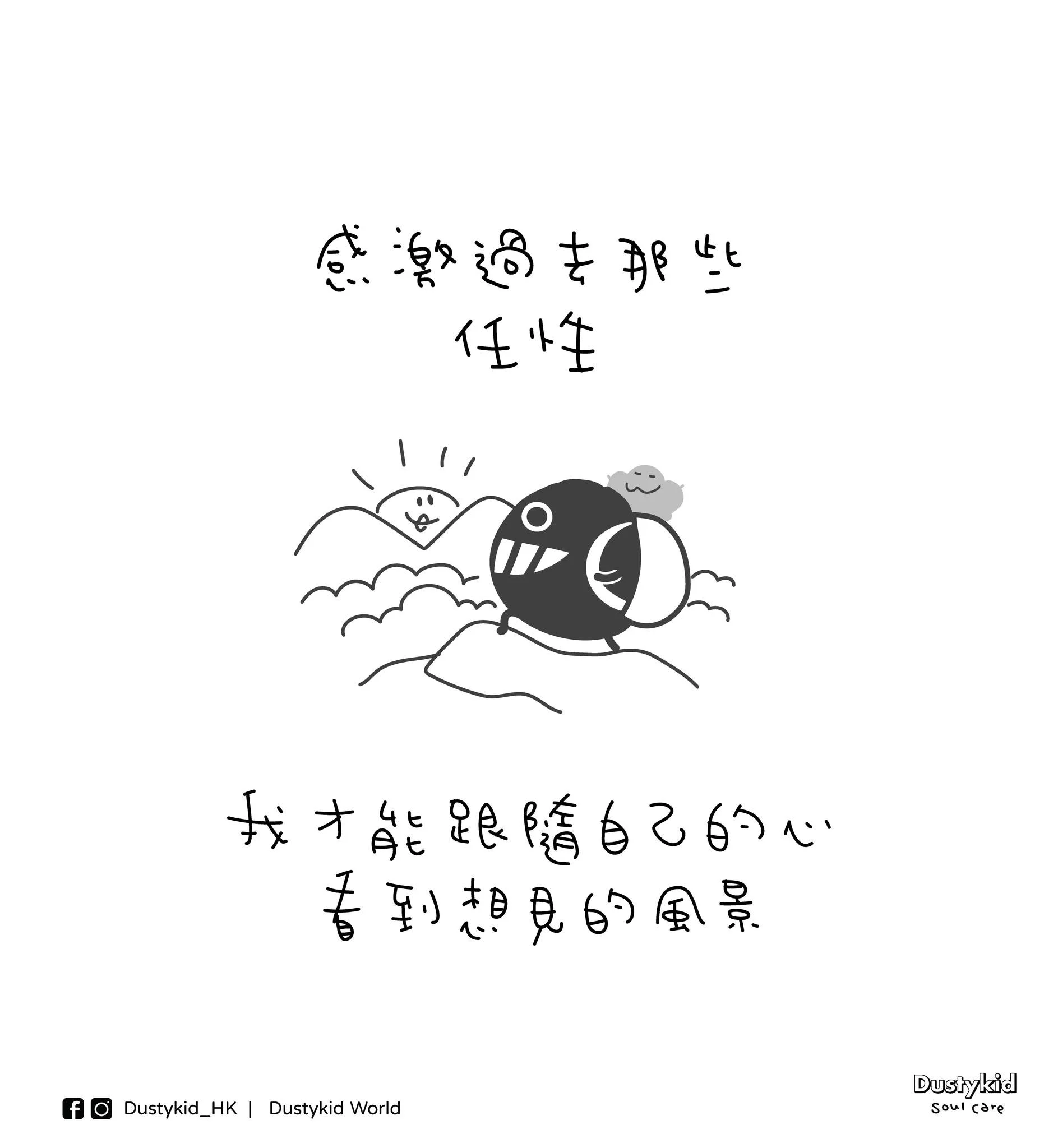Thomas Gianni畫

(下)扉頁上作者的紅筆題字

彌娜中招 殭屍新娘
吸血殭屍 星夜出動
月色女妖 日出退避
女妖取血 捉妖天師
Robert Place畫
絕大多數的恐懼存在於想像之中,而沒有什麼能夠比黑夜更能刺激和引發我們那無邊無際的想像。
⚡ 文章目錄
月宮寶盒透陽光
五年前的一個五月天,我因事路經紐約皇后區的加爾瓦略山墳場(Mount Calvary Cemetery),忽然雅興大發,故意不乘搭公共汽車,卻要穿過那遼闊的墳場去到在另一邊的街道。一大片平坦的綠草地上面排列着灰白四方的墓碑,在陽光的照射下越發顯得浮凸有致,叫我聯想到小時候玩過的海陸空棋盤遊戲;我那天自覺元神充沛,心情愉快,透明的陽光灑滿一身,雖然知道置身於生死大限的所在,卻完全沾染不着死亡的陰影:一切和我無關,我只是路過看看而已,並且還情不自禁輕輕地哼起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難怪有這一說:越是無知自私的人越是快樂。我邊走邊看,尤其吸引我的是那些偶然聳立在藍天白雲下的陵墓,有穹頂、尖頂、平頂,像一座座小聖堂,也有作長方形的,四周飾滿了浮雕和染色玻璃窗,牆腳爬滿了野草黃花,乍看彷彿是《阿拉伯之夜》裏面的月宮寶盒。我上前一看,玻璃門倒是鎖着的,門後是一道屏風影壁,我不知道哪裏來的膽子,雙手貼着玻璃門,花了好些時間努力調整視線,但是始終無法看到影壁後面的靈柩,只是在縫隙間影影綽綽看到了有陽光透過瑰麗的染色玻璃窗,把彩影靜靜地投射在大理石地面上;相信死者也是同樣的寧靜吧。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舉止失當,就畫了一個十字聖號,匆匆離去。
萬般恐懼向死亡
我事後告訴老伴,並且說:「你是知道我的,平常膽子最小。」老伴道:「這也不算什麼,若果當時是夜平三更而你又獨自一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老伴也怕黑,睡前先把位於睡房和浴室之間的房間的那道門關上了,省得半夜小解要經過和面對黑漆漆的房間;白天好端端的房間,夜晚忽然就變成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在風雨交加的夜裏,窗外樹影幢幢,樹影之外就是那洪荒的宇宙,那不可知的恐怖說不定就忽然掩至,而其實一切大大小小的恐懼卻原來皆指向死亡。
萬般恐懼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可知和不可知的。如果我說:「隔壁房間有一隻老虎。」你會產生第一種恐懼。如果我說:「隔壁房間有鬼。」那可是完全不同類的一種恐懼。人類文明的一大目的,就是將各種不可知的恐懼馴服成可知,通常是依靠科學的研究精神,冷靜面對,深入理解。而在同時,對待死亡的不可知和死亡引起的終極恐懼,我們還是有辦法去面對或化解,或依靠藝術的距離,或依靠幽默的態度。像洋人的萬聖節,就是一年一度公然開死亡的玩笑,大人小孩扮鬼扮骷髏,嘻嘻哈哈通街走,彷彿死亡也只不過是一場遊戲罷了。這未嘗不能對死亡的恐懼起了一點平衡作用。法國聖女德肋撒小時候曾經在夢中遊家中的後院,發現貯存雜物的小木房內有兩隻小魔鬼在木桶上跳躍作樂,腳上還有鐵鍊;德肋撒透過窗口觀望,一點也不害怕,倒是兩個小魔鬼一見德肋撒,立即跳下木桶,慌張地找地方躲藏。純潔的心靈,即使面對最原始的邪惡,亦一無所懼。
吸血殭屍偽君子
至於吸血殭屍,倘若遇到了反而不用怕,因為現成的應付方法多的是,十字架和蒜頭只是其中的兩樣;怕只怕吸血殭屍化成正人君子混在我們中間,那才防不勝防。希治閣的Shadow of a Doubt(1943年,港譯《辣手摧花》)裏面,有位兇手名叫查理斯,專門向富有的寡婦下手,並且說她們不外是肥胖喘氣的畜牲,整日穿金戴銀,飲食作樂,對社會一無貢獻。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星,表面上也是個斯文有禮的君子。但是希治閣匠心獨具,在很多細節上暗示查理斯是隻吸血殭屍,例如說,在他認真談話之際,聲音轉為陰沈。有時見他獨自躺在牀上,閉上眼睛,彷彿陳屍,但是一旦窗簾放下,光明隱退,他的一雙眼睛就霍然睜開。聰明的畫家在電影海報上更在查理斯的巨大身影加上一隻殭屍一般的手掌,五指微曲,伺機出擊。
福爾摩斯破奇案
福爾摩斯的作者柯南道爾寫過一個短篇叫《薩塞克斯的吸血殭屍》(The Adventure of the Sussex Vampire,1924年),內容描述丈夫發現妻子吸幼兒的血,以為妻子中了魔道,成為吸血殭屍,找福爾摩斯去查證。原來這妻子是填房,前妻遺下一名十五歲的殘廢兒子,妒忌父親鍾愛同父異母的幼弟,圖謀用毒鏢將他殺害。妻子不忍將這駭人的真相向丈夫揭露,一方面又要暗中替幼兒吸除毒血,竟然招致天大的誤會,卻又解釋無從,因為她深愛丈夫,不忍傷害他和長子的感情。粗看故事大綱,橋段似乎有點牽強,但是大師寫來依然抽絲剝繭,合情合理。反正真實的世界往往比虛構的小說更為奇異,而把好人誤會為惡鬼的例子也並不罕見。
一般人對吸血殭屍這類題材有興趣,可以是一種保持距離的觀看欣賞,那是藝術的層次,也可以是為了尋求一點刺激,故意接受驚嚇,那是一個遊戲的層次,因此依然可以說是健康而無害。這裏的一套吸血殭屍塔羅牌,由美國的Robert Place編繪。他綜合了許多的吸血殭屍文學作品,除了《卓古拉》之外,還有愛倫坡和拜倫的作品,堪稱內涵豐富,繪工也別具一格,頗有彩色木刻版畫的風味。書的扉頁上有作者半開玩笑的卓古拉名言:「血就是生命。」並有他的親筆簽名,特別用紅筆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