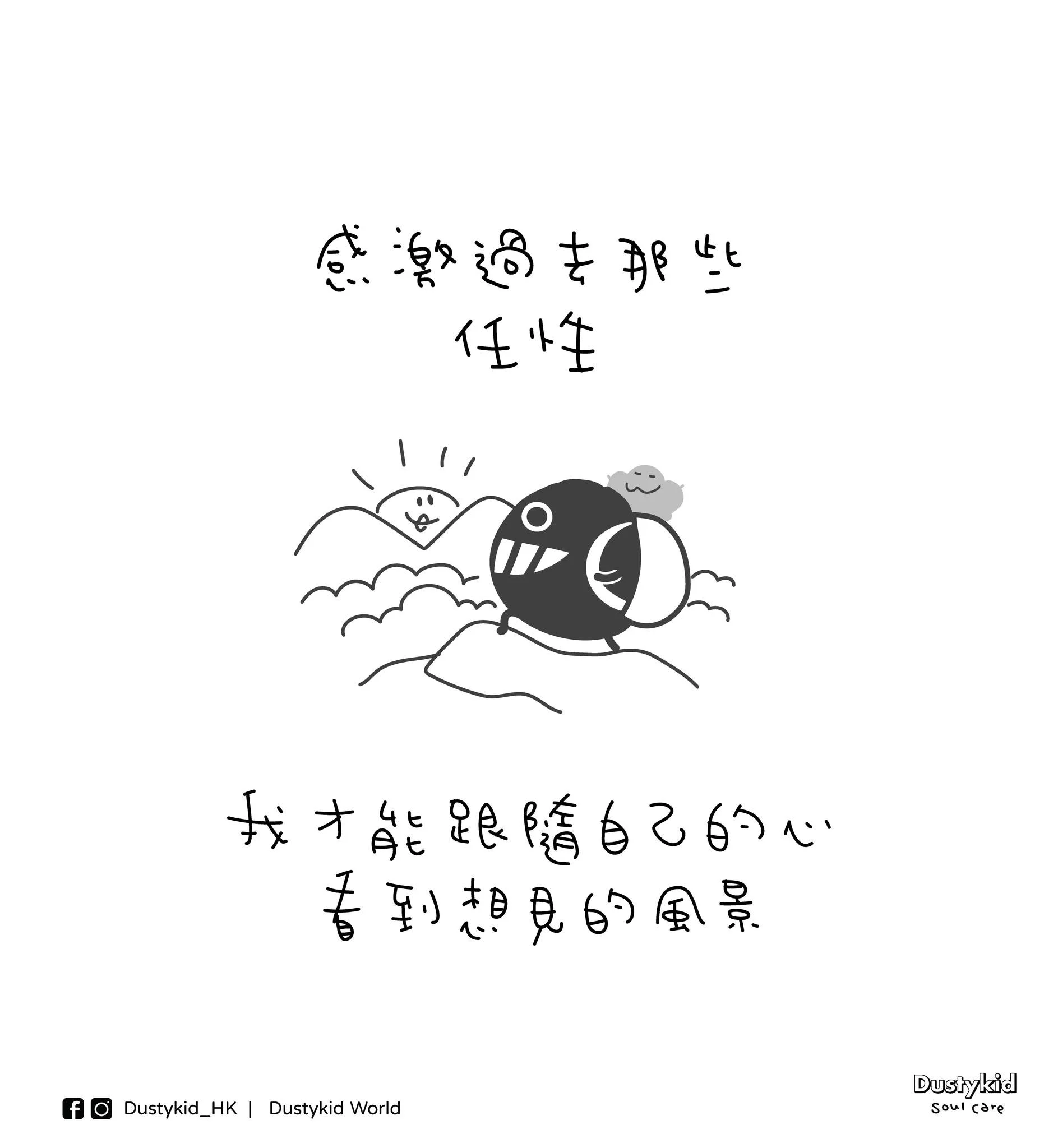你想知道何謂有緣無份?請看看垮掉的一代和我。
在美術學院打發時間那幾年,女同學提起某位教文學課的老師,輕則不吝流露叫春貓表情,重者即席複製愛情動作片全套功架,平日熱情奔放的固然踴躍擺出蕩婦姿態,就算胸前掛著淑女招牌,也不惜撕破臉皮自毀形象,將暗中也想變壞坦誠公諸於世。張愛玲《同學少年都不賤》裏天真燦漫的寄宿生,「各人有各人最喜歡的明星,一提起這名字馬上一聲銳叫,躺在床上砰砰蹦蹦跳半天」,一九七幾年在加州磨鍊藝術細胞的女流氓品味卻不分彼此,縱使沒有讀過《紅樓夢》,亦偷龍轉鳳演繹曹雪芹的「千紅一窟萬艷同悲」,化悲為喜集體把三千寵愛灌注在同一朵鮮花。
呃,對不起,四十幾歲的中坑,絕對不應該稱為鮮花,不嫌刻薄,簡直是老花。名叫Michael McClure,我聽都沒聽過,怕被恥笑當然不動聲色,默默記下事後詢問當時的拖友。他略表驚訝:「垮掉一代的詩人啊,和堅斯伯平起平坐的,你怎麼不認識?」大概立刻扣分,甚至譴責自己不帶眼識人。
起了底,卻依然沒有興趣修他的課,白白失去親吻現代文學的良機。只記得一次展覽開幕酒會,他穿了一套淺青檸色的麻質三件頭出席,漂亮到不得了,完全明星派頭。
垮掉一代大本營城市之光書店位於三藩市百老匯道,就在唐人街邊皮,黃姓香港同學周末在金鳳酒樓客串帶位,我們常常相約打烊後去基吧跳舞,住奧克蘭的我提早過海看下午場,散場之後無所事事,有好幾回順腳兜進書店消磨時間。出版於微時的詩集被尊為鎮店之寶,隆而重之擺在收銀枱旁最矚目的書架上,因為曾經是禁書,翻開來聚精會神搜索色情字句,就像十三四歲慕名拜讀羅倫士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郭良蕙的《心鎖》,也同樣一無所獲。比較熱衷下去地庫徘徊,樓面既低,架與架之間的通道又窄,那麼瘦都周轉不靈,幽暗燈光下和打書釘的同道中人擦肩而過,呼吸自然而然陷於急促,空氣中充滿神秘和刺激,彷彿預先練習即將在同志交際場上演的喜相逢或相見爭如不見。
奇怪,似乎清一色單身男顧客,印象中沒有見過女性。莫非真的有鬼?無論如何,行正桃花運沒我份,邂逅有緣人爽約黃金鳳的重色輕友情節從來不曾出現。多年後,倒在百老匯道另一家書店有艷遇,交往了一段短時間,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因為對方是亞洲人,當時難得的。洛杉磯土生土長,家傳之寶離奇英偉──我覺得可能該地自來水含有壯陽礦物質,否則解釋不了為什麼認識的洛家村民無一例外身懷巨物。
不但垮掉的文字讀不進去,連垮掉的影片也看不進去。有一部《採吾菊》,師兄師弟傾巢而出,萬綠叢中再加尚未現身《去年在馬倫巴》的黛芬西莉,是美國地下電影的珍品,聞名已久,今年香港電影節赫然榜上有名,於是興高采烈一看究竟。克魯亞克撰寫兼朗誦的旁白,聽了兩句已經昏昏欲睡,西莉小姐演招呼豬朋狗友的女主人,恍如《主婦日記》前傳,雖然自封鐵粉,也不能集中精神深究,和爵士樂同步的節拍更盡情發揮催眠副作用,迷迷糊糊間,放映室就亮了燈。
幸好一再按門鈴的不限於郵差。龐比度中心的垮掉一代展覽,影片循環投射牆上,我一坐下來不捨得起身,連續看了三次。最後一次,純粹為了聽先前充耳不聞的主題曲,無厘頭的歌詞可愛極了:
採我的菊花
傾我的杯
我所有的門都打開了
割我的思維以椰子
我所有的蛋都爛了
唱歌的女子叫Anita Ellis。上網一查,哎呀,原來《蕩婦姬黛》膾炙人口的《都怪敏吧》,她是女主角烈打希和芙的幕後代唱。舊相識啊,失覺失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