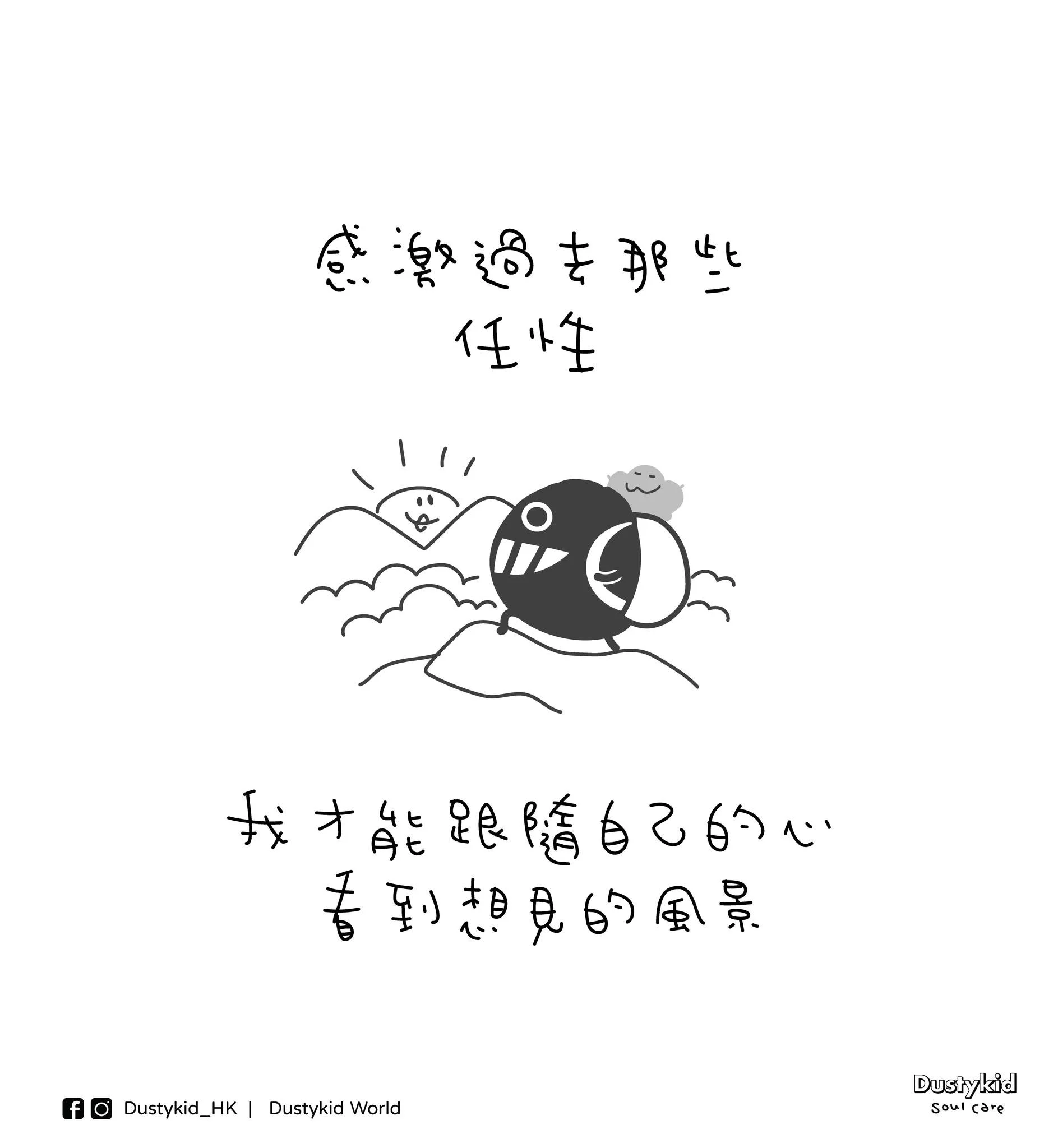新加坡摘下第一面奧運金牌,為國爭光的是個二十一歲泳手。媽媽在長途電話提起,語氣不特別興奮,只說大熱天時衣錦榮歸的新科狀元遊街,我弟婦帶了小姪女趁熱鬧,言下微微有種「現在的後生,真是……」的喟嘆。
該地從前引以為傲的運動項目似乎是羽毛球,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大概因為得過獎,中產住宅區私人球場屢見不鮮,每逢夕陽西下噼噼啪啪此起彼落。亞洲人體魄一般稍遜白人黑人,踢足球打籃球先天上佔弱勢,羽球毋庸軀體硬拼,身手靈活便可以,超英趕美機會較高。性質相若的乒乓也流行,學校小息最熱門的遊戲就是打乒乓,不過脫殖獨立後並沒有被捧為「國運」,想是形象太中國的關係,不能不避嫌。人口之中華裔雖然最多,對中華文化的景仰也深,但是大陸赤化大家聞共產黨色變,朝野彌漫染紅的恐懼,左仔被打壓得厲害,識時務者為俊傑,當然不會明知故犯。
既然是四面環海的島國,訓練泳手事在必行,起碼普世觀念是這樣,就像住在有隨時遭浪花吞噬危險的地頭,為了求生不得不向水族拜師,當不成美人魚也要當熱帶魚。剛認識法國前度時問他會不會游泳,他面露驚訝答:「當然會,我出生的地方是個小島」,一加一等於二,放諸四海皆準。
然而我出水能跳,入水卻不能游,現在這身三爬兩撥就必須站着換氣的低等工夫,還是遲至八十年代才在香港南華會學的。說出來好笑,我們家不但離海不遠,爺爺名字有個海字的緣故,大門旁刻着「海廬」二字。步行十分鐘是沿海的加東公園,秉承殖民地中西夾雜傳統,park音譯成廣東話「北」,黃昏日落後氣溫稍降,大人常常帶我和弟弟去加東北散步。海浴場以堤壩方方正正圈着,潮退我們在沙灘檢貝殼,潮漲在堤壩上兜一圈,從來不行下水禮。公園閘外有流動小販賣零食,兩塊長方形餅乾夾成三色三文治雪糕,紅的是草莓,白的是雲尼拿,啡的是朱古力,又香又甜又豐盛。後來填海,海岸線大規模往外移,公園形同虛設。九十年代回家探親,新認識的朋友聽聞我家地址大表羨慕:「公園對出去的填海區入夜後是同志雲集的野戰場耶!」吃過晚飯帶我去參觀,果然名不虛傳。
有一個時期,周末舉族去樟宜沙灘野餐游泳,姑媽姑丈表姐表弟浩浩蕩蕩一行二十幾人,成年後我對集體旅行恨之入骨,不是沒有理由的。坐一架密不透風的貨車,號稱「豬籠車」,不但顛簸而且悶熱,某次回程胃裏一陣翻騰,沙特名著《嘔吐》人肉搬演,早前喝的凍咖啡悉數吐出不特已,留在口腔的惡臭驅之不散,自此戒了這款黑色飲品。旅居巴黎後,新知舊雨見我既不喝紅酒也不喝咖啡,莫不贈以暴殄天物的鄙夷眼神,久而久之,凝聚成犯罪感,於是晚餐開始喝酒,一點一滴,漸漸練出幼稚園級酒量。咖啡比較困難,試了幾次徒勞無功,直到前年在翡冷翠過聖誕,天寒地凍無以為繼,茶喝多了頻密上廁所實在不方便,在烏菲茲美術館排長龍那天忍不住喝了一杯卡普奇諾,沒有反胃之餘竟然上癮,如今幾乎天天都喝,以報仇的方式狠狠奪回失去的時間。
其實赴三藩市唸書之前,在新加坡企圖學過游泳,地點是中華游泳池,基於什麼原因上了幾堂半途而廢,卻一點也記不起來。恐怕是當時尚未流行有近視度數的潛水鏡,脫了眼鏡在水中無所適從,慌失失毫無樂趣可言,連教練的五官也沒有印象。視覺故障,一直困擾我體格方面的發展,所以隱形眼鏡真是四眼仔救星,要不是有它打救,後來不會敢貿貿然跑去習舞。那,當然是另一系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