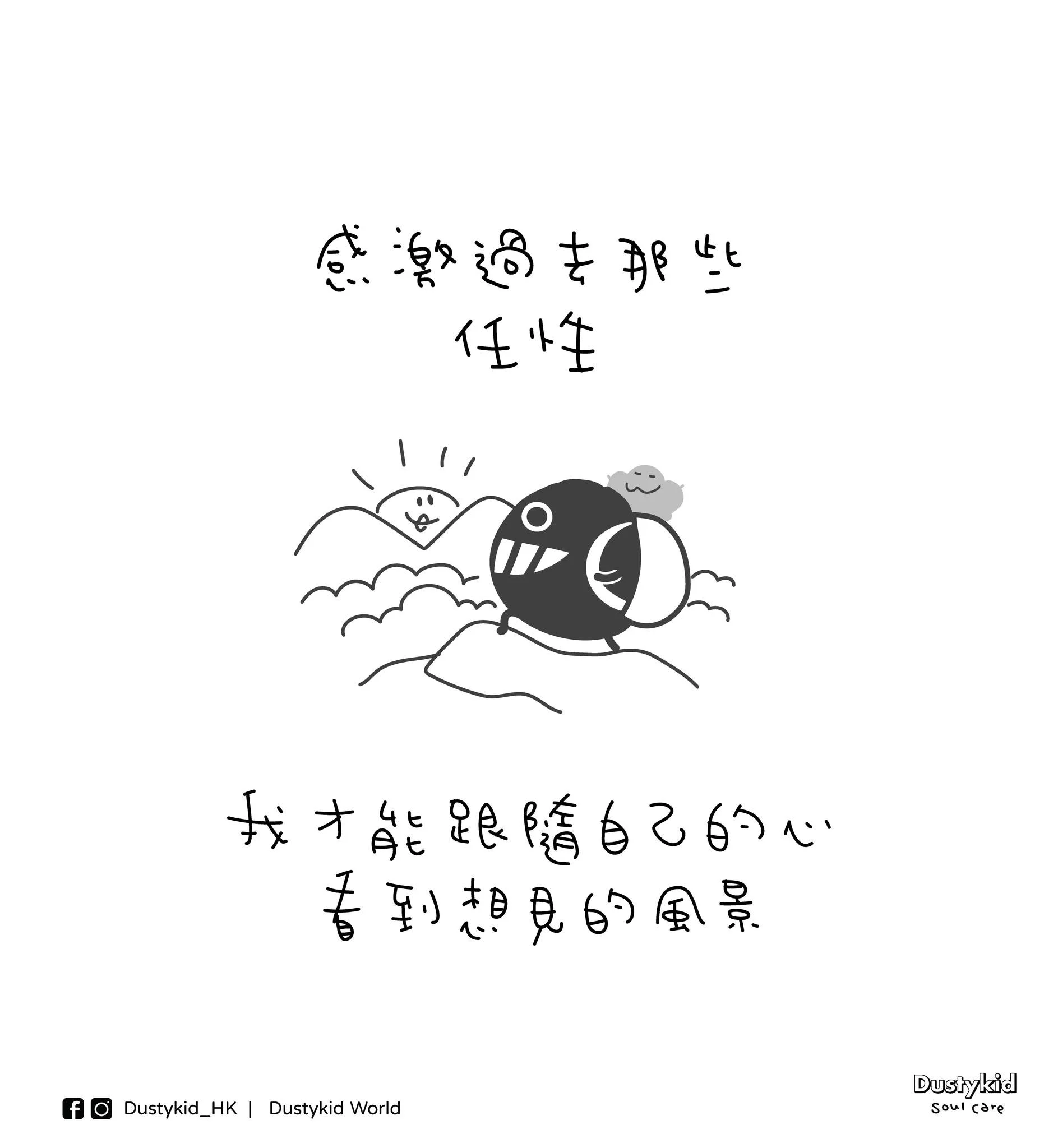真奇怪,同樣語言不通,靠讀了故事簡介坐在台下運用幻想力二次創作,海老蔵領銜主演的《柳影澤螢火》無動於衷,反而猿之助擔綱的《荒川之佐吉》初看已經令我淚盈於睫,翌日重看更加感動,幾乎有資格和前後左右的日籍少婦大媽分庭抗禮,需要掏出手帕醒醒鼻涕,才能漂亮地離開歌舞伎座。自身難保的小流氓仗義收養被遺棄男嬰,發現他原來雙目失明仍然悉心照顧,幕起幕落,轉瞬小孩長到七八歲,雖然伸手不見五指,卻出落得聰明伶俐,聽到遠遠的腳步聲就知道爸爸回家,歡天喜地奔到門口迎接。有一天和武藝高強的浪人較量,居然擊斃對方,神差鬼使被黑幫大佬重用,旁門左道的榮華富貴縱使帶來錦衣玉食,他並沒有埋沒初衷,外面的世界殷殷呼喚,唯有忍痛把小孩送回親生媽媽處,闖蕩江湖浪跡天涯。
這樣的庶民劇,你不可以說它缺乏高潮,但始終有種日常的恬淡,接近採菊東籬下境界。我想起《男人之苦》那個吊兒郎當的寅次郎,有情還似無情,相見爭如不見,一年兩度的長壽系列,每回結局都混雜了他的惆悵和釋然,世俗眼中的一事無成兩袖清風,調整為使人羨慕的生活態度。男主角渥美清二十年前逝世,延續了四十八集的日本路線劃上句號,長情導演山田洋次後來移花接木,將未曾拍攝的劇本改成向美好時光致敬的外一章,我一直沒看過。假如決定和這個小人物再續前緣,猿之助倒是飾演寅次郎的上佳人選,和高大英俊背道而馳的賣相,正好隱沒在茫茫人海,偶爾浮出溫柔和慈悲,就像印證生命仍然充滿可能性,得其情者哀矜勿喜,只有感激。
上次在新宿紀伊國屋書店見到一本寅次郎專書,詳盡介紹戲中人二十多年間冬夏兩季遺下腳印的小城小鎮,按圖索驥的誘惑雖然撲面而來,自己知自己事,翻閱後只好放回架上。除了早安多謝再見和從愛情動作片學到的「二姑二姑」,日語一概不諳,加上老態日漸龍鍾,只差尚未出動手杖,而且理想的萬能書僮遲遲未如波提切利的維納斯在水平線踏着蜆殼誕生,怎麼能夠暢遊四國放心吃喝呀?嗚嗚嗚。
這家老書店是東京之旅必到之地,深度讀書人讚不絕口的神保町一點興趣提不起來,潮人追捧的代官山蔦屋再好,鑑於不順路也只參觀過一次。新宿不但交通方便,當然還有感情因素托底,由七十年代末初降羽田機場開始,就懂得摸上門吸收養料,一提紀伊國屋,味蕾自動釋放寶礦力的回憶。八十年代打完書釘順腳到數街之遙的伊勢丹選購三宅一生孖煙囪,繼而操往二十四會館進行社交,靈慾分家各得其所,精神和物質大大滿足。那時華燈初上,三井住友銀行外的行人道,總有個其貌不揚的女相士擺檔,將指點迷津當作職業的她縱有本事目測顧客的過去未來,對自身前程卻似乎沒有什麼把握,眉頭永遠微微皺起,面前的空凳從來不見屁股填上。一般人心目中的東京是時尚現代大都會,很難想像古老的迷信會像顆美人痣,出其不意點綴街頭吧?
這回如常先在樓下翻翻新鮮出爐雜誌,為封面印了個半裸洋漢的《泰山》體臭專號忍俊不禁,讚歎恐怕只有在日本,種族歧視才可以這麼若無其事;跟着搭電梯上七樓,準備瀏覽比較不受語文困制的美術、電影和歌舞伎,駭然發現專櫃全部洗牌,要找的書籍無一盤踞在兩個月前的位置。不得不承認,我其實是隻憑記憶摸索方向的野獸,熟悉的地標一經改動,馬上出現迷途危機。泛起的驕傲,略似張愛玲《重訪邊城》寫自己穿了土布衣裳去登記戶口,「一個看似八路軍的老幹部在街口擺張小學校的黃漆書桌,輪到我上前,他一看是個老鄉,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問了聲:『認識字嗎?』我點點頭,心裏很得意。顯然不像個知識份子。」
當然不是知識份子。買了橫尾忠則的《幻花幻想幻畫譚》和取自浮世繪的《江戶之惡》,都以圖畫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