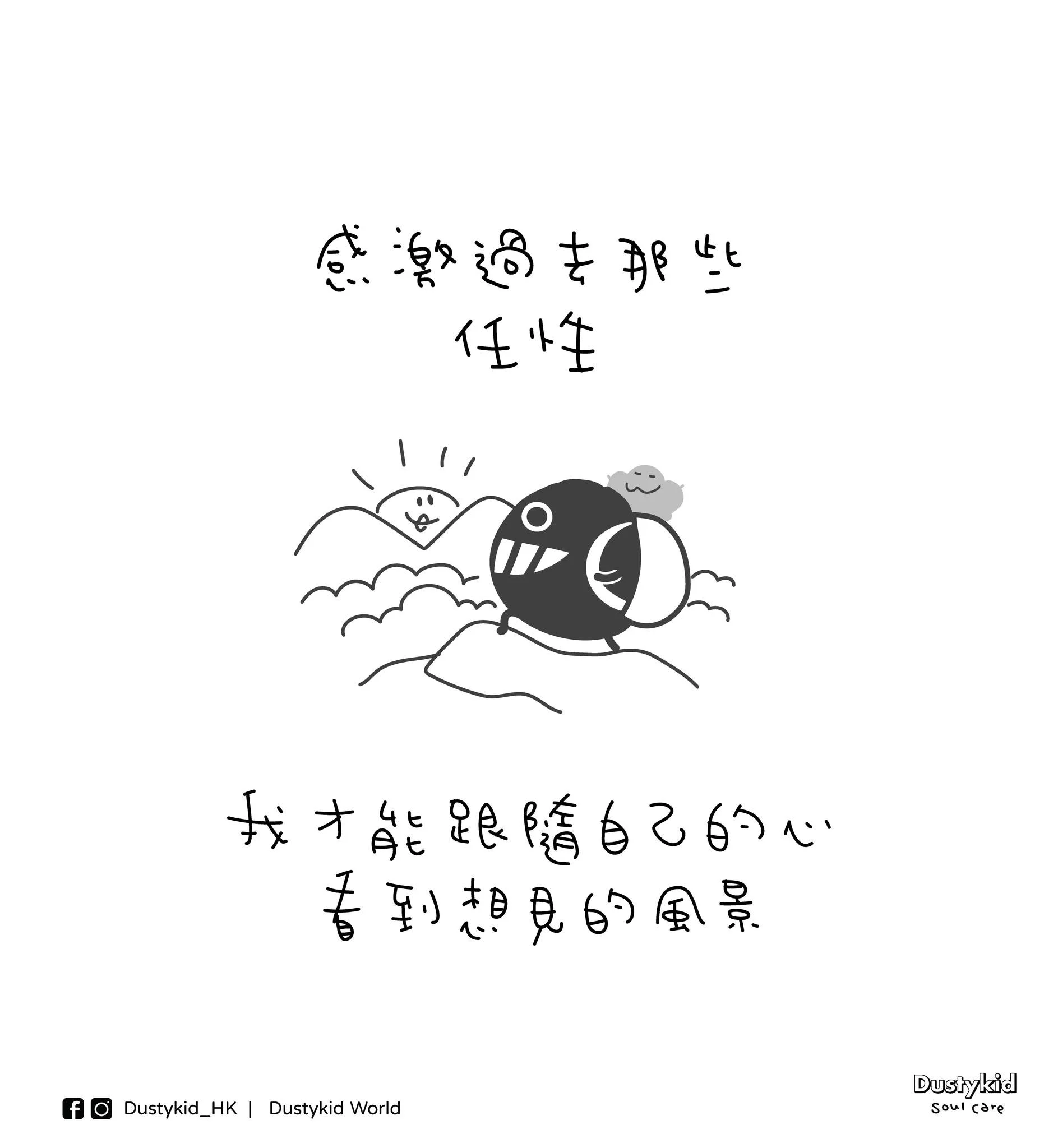起程去東京前,隨手整理了一下廚房。好日不舉灶的關係,過期食物不多,那樽麻油可能尚未至於變質,但太久沒有下麵,瓶口微微積着灰塵,實在有礙觀瞻,想也不想就扔進垃圾桶。旁邊有個白色小膠袋,裝的似乎是吃剩的餅乾,打開一看,卻是塊生薑。咦,既不煎又不炒,家中何來此物?枯腸搜索一輪,終於找到答案:大半年前咳嗽,醫生開的藥水喝過好了五六成,但是纏纏綿綿總不能斷尾,正方如川貝枇杷膏偏方如鹽燉橙一一試驗,仍然時好時壞,有一晚到張畫家府上吃飯,他二話不說用水煮了個羅漢果,竟然立竿見影,整晚天南地北滔滔不絕,氣管幾乎沒有作反。臨別塞兩個存貨給我,並且囑咐「最好加片薑」,我深知這些土產物離鄉貴,耍手擰頭百般推辭,奈何他一定要我收下,盛情既然難卻,一不做二不休,翌日言聽計從去超市購買號稱百辣雲的草本植物,以免辜負贈藥者一番好意。
切了兩片束之高閣,忘得一乾二淨。陳年老薑,連看門口的功能亦欠奉,不是廢物是什麼,正想送它進最後歸宿,忽然發現左右兩端各自萌長幼芽,不由得一怔。困在密不透風的膠袋裏起碼七八個月,生命力怎會如此頑強,逆境中默默掙扎着,兵分兩路企圖活出另一個春天?憐憫油然而生,於是從架上拿下一隻磁碗,注入幾分清水,把它安置在內。不敢指望它會天天向上,綠拇指是天生的,我一向沒有,小時候家裏前園栽花後園種果,唯一的記憶是拾起鳳凰木墜落的花蕾浸水,第二天開出艷熾熾的大花,泥土完全引不起好奇。後來在三藩市與A同住,他為屋子後有片土地莫名興奮,問准了房東,翻土挖石澆水種草,在一角開闢小菜園,我偶爾的幫忙只能算是應酬一你別以為美國俚語沒有「坐享其成」,肢體語言發放的蔑視才厲害哩,連失聰人士也如雷貫耳。
從東京回來,半碗水吸乾了,一兩吋高的芽開始抽葉,那種初生的翠綠非常清麗,觀察半天愛不釋手,這才誠心誠意供奉起來。放在廚房窗邊,每天早上起來加點水,打開窗讓它呼吸新鮮空氣,一陣淡淡的辛味幽幽升起,像是笑口盈盈說謝謝。千萬別誤會,吃了豹子膽我也不敢自比賈寶玉,林妹妹糾纏不清的還淚尤其害怕,只不過希望成全它爭取生存權利的志氣,它盡它的本份,我也盡我的本份,各自修行兩不拖欠,一如三四年前米可諾斯短暫的西瓜故事。
希臘小島類似的住所並不罕見,圍牆內散佈兩層高度假屋,單位面積不大,勝在門戶自立,我們租住的一間特別清靜,打開落地玻璃窗是個剛剛擺得下一張小桌的私人花園,坐在那裏早餐或晚餐舒服極了。夏天沒有什麼比吃西瓜愜意,街角小市場有得賣,劏開可以吃兩三天,冰凍之後更加美味。種子扔在身旁泥地裏,有一天從海灘回來,晾起洗淨的衣物,忽然見到土中冒出一排雙葉嫩芽,連忙蹲下細看。此後日夜留心,簡直比觀賞魔術表演更有趣,一個多禮拜的時間,長得非常快,令人想起「生命的奧秘」之類抽象的形容。臨走的一天如常澆水,滿心依依不捨,那裏來來往往的貓很多,家貓野貓都有,撒泡尿磨磨爪,初生的植物凶多吉少。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第二年再去,一如所料影蹤全無。還是其實活到冬季,完成了份內的循環?
生薑越長越高,恐怕單單靠水不夠營養,況且另一個夏天假期又要開始了,一碗水無論如何不能維持兩星期,不得不考慮更長遠的計劃。「入土為安」指的,倒不一定是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