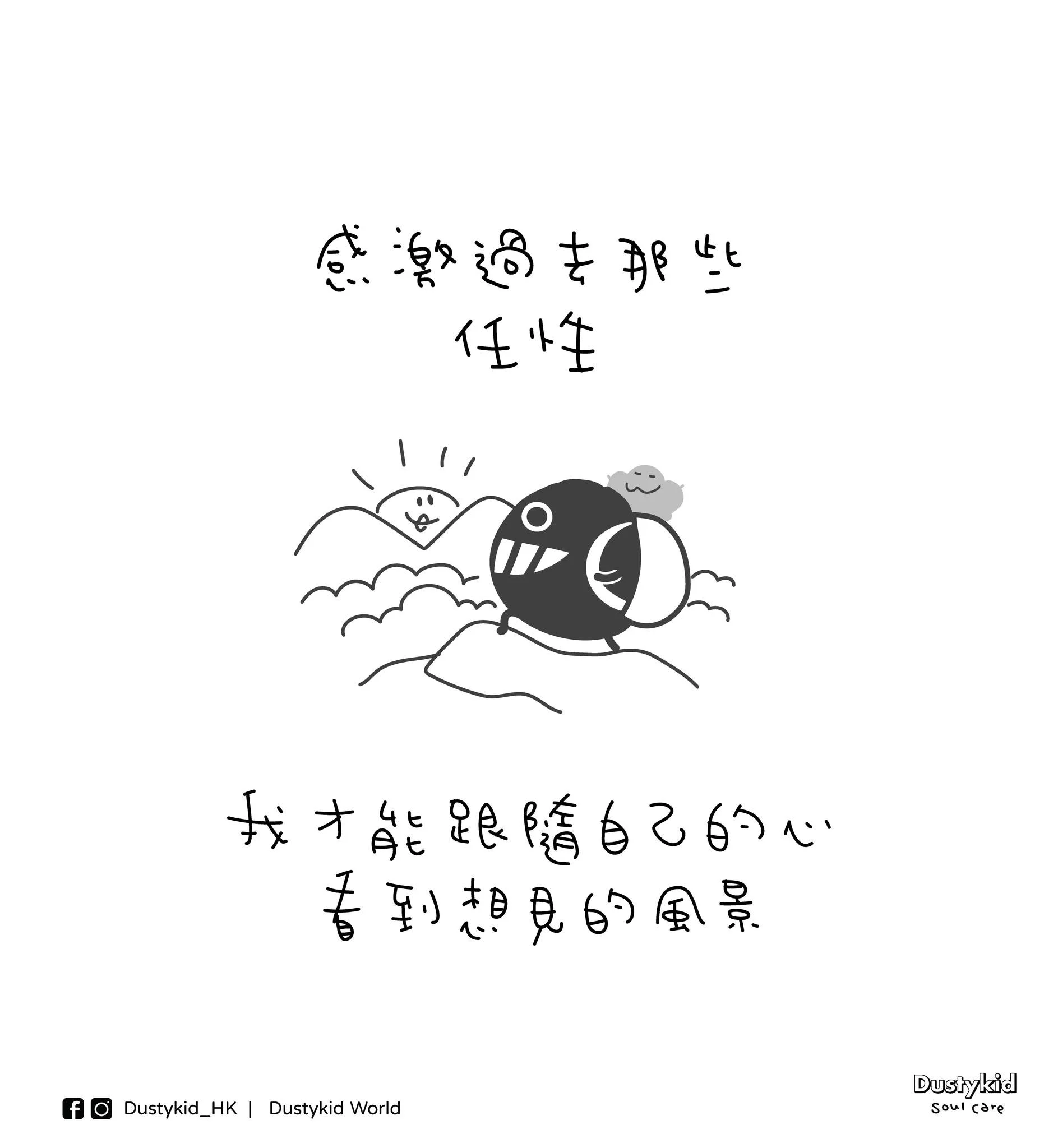翩娜包殊逝世,不經不覺已經七年了。巴黎城市劇場仍然年年邀請她的孤兒舞團演出,節目表向來掛她名字,今年換上「烏珀塔舞蹈劇場」招牌,教我一陣黯然。
跳千禧年遠赴巴西創作的《水》,首演時認為不怎麼樣,她的旅行系列除了少數作品如《巴勒慕巴勒慕》,我都不特別喜歡,總覺得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味道太濃,遊戲人間也還罷了,不可原諒的是馬虎交差。這次重看卻大大改觀,雖然不及西西里的日與夜精彩,伊巴尼瑪海灘的微風倒自有一股俏麗,在不曾浸過鹹水的大鄉里眼中,確實盡了導遊的責任。
或者,是那首源自《黑奧菲爾》的插曲,把我帶到南洋小島遺失的晚上,以致忽然溫情氾濫吧。電影是十六七歲在新加坡電影協會看的,故事裏的希臘神話成分渾然不覺,只為色彩繽紛的嘉年華傾倒,巴莎露華節拍的音樂深深印在耳膜,到三藩市後念念不忘,買了原聲帶唱片來聽。同期看的《男歡女愛》新加坡譯《孤男寡女》,其實更吻合劇情,配樂風行一時,插曲之一也是巴莎露華,簡直是巴西的最佳旅遊大使,不動聲色將廣告植入旋律之中。
又或者,因為知道城市劇場即將閉門維修,難免依依不捨,莫名其妙加了感情分。八十年代末第一次進入包殊的世界,就在這個舞台,康城影展後路經巴黎,王姓文藝青年善心大發替我找到一張門票,跳的是《康乃馨》。當天下午借題發揮去Agnès b總店買了件黑色的麻質外套,興高采烈參與其盛,後來回到香港嫌衣袖略長,拿給裁縫改,結果剪得太短,再也不能穿,心痛筆墨難以形容。
直到十多年前,城市劇場營運依然非常隨和,氣氛接近法國人所謂的baba-cool,等於我們口中業已人間蒸發的「嬉皮士作風」,院方歡迎座位欠佳的觀眾臨開場自動換位,畏高者乾脆省下爬山入座的氣力,站在前台一旁等空位,如果插針不入,一屁股坐在甬道的梯級上,帶位員完全不介意。中場休息不檢票,我試過出去帶領買不到票的朋友打戲釘,雖然只看下半場,一樣滿心歡喜。改朝換代後規矩也改了,嚴禁席地而坐,說是有違消防條例,不過照舊鼓勵高山族往前遷移,貫徹一種「有福同享」的波希米亞特質。
《康乃馨》二零一一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重看。原本打算看一場,不知道誰多了一張票,問來問去無人認領,於是尾場又看一次。燈光暗下去了,後一排及時趕到的兩個人迅速入座,經過背後輕輕打招呼,回頭一望,是W和她的兒子,戴着口罩,幾乎認不出來。散場匆匆講兩句,因為要送小朋友回家,當然不考慮和我們宵夜。再也沒有想到,那是我和她的最後一面。
九三年尚未在亞洲打響名堂的包殊赴港演出《1980》,主辦當局為了宣傳,開鑼前的下午在文化中心鄭重招待記者,甚少應酬的編舞家從善如流作出短短介紹,跟着就請大家參觀鋪在台上的草皮。那次也碰到W,她感到意外因為我老老實實不屬於報界,我感到意外因為不知道她對舞蹈有興趣,相請永遠不如偶遇,過對面男青年會咖啡座聊了半天。啊,時間到什麼地方去了?正如Fairport Convention那首歌所唱的,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