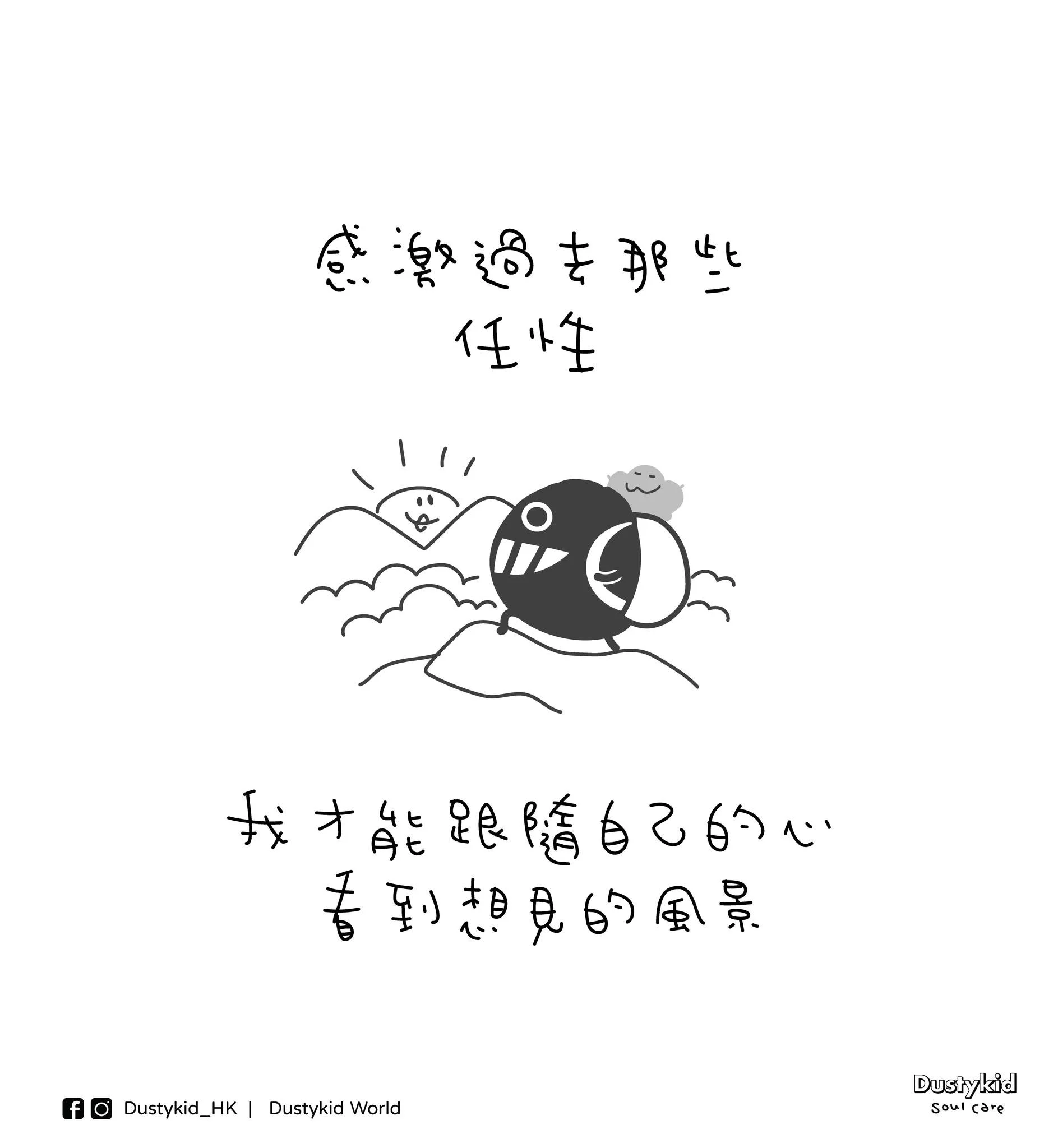上環這幾條古舊的橫街,周末深夜有點男同志天堂風貌,人山人海的酒吧插針不入,顧客三三兩兩散佈門外行人道,臉孔缺乏天使氣質沒關係,最重要有魔鬼身材可以展覽,雖然不及台北紅樓東京新宿熱鬧,在香港亦算僅見。那個鐘點我通常已在牀上準備和周公幽會,無暇企圖開拓交際網,有一晚去中大看完崑曲折子戲,出了地鐵站由永樂街拐進文咸東街走回住所,遠遠就聽到細聲講大聲笑,這些青春小鳥平日穿戴整齊上班上學,大鑼大鼓反串不至於,帶着喬裝況味則恐怕多少免不了,只有處身同類羣中才放開懷抱盡情招搖,從囂張中學習驕傲。
走過脂粉叢後有個小青年蹬蹬蹬追上來,操英語,一聽就知道是日本人:「請問,有一間基吧,動物園,在附近嗎?」真是活見鬼,額頭又沒有鑿字,怎見得我是識途老馬!樣子殷實語氣誠懇,不像是白撞搭訕,於是教他下個路口轉左,在平行的蘇杭街再轉左。他大概暗罵香港人沒禮貌──在日本問路,如果目的地在附近,他們一般會把你帶到,不會單單指手劃腳這麼冷漠,但我還沒有從悱惻纏綿的《幽媾》醒過來,只好對不起禮儀之邦的遊客。
八十年代初來的時候,基族蜂擁而往的旺區在中環,我第一個周末就被朱同志捉了去DD消遣。她有個朋友是高級警花,辦公室在數步之遙的中央警署,飯碗攸關,出入這類場所不能不小心翼翼,聽聞三藩市來了基佬不禁眉飛色舞,馬上邀約共赴舞池。之所以那麼雀躍,全因為左右傍着「護花使者」作掩飾,就算被同袍碰見也不怕,也不管這把「鬍子」的男子氣概比粗豪的她差十萬八千里。忘了是不是先在希爾頓酒店的貓街咖啡座集合,那時「佔中」的兄弟姐妹,華燈初上喜歡約來這裏聚腳,齊人才操往蘭桂坊,皇后大道常見成羣結隊的皇后,個個花枝招展體態風流,有種錢塘名妓出巡的綺艷氣氛。
此調早已成絕唱,希爾頓沒有了,DD沒有了,耀眼的青春也沒有了。忽然想起台灣J小姐講的笑話:「你別看影壇大姐大強悍威武,年輕時比美胡茵夢哩,她自己說的,『當年我也稱得上靈氣逼人,可現在呀,靈沒有了,氣也沒有了,只剩下個逼!』」不過男同志的保養向來出神入化,就算靈和氣悉數蒸發,花容月貌還是不會遭歲月洗劫的,譬如數星期前三藩市舊同學黃某訪港,約在IFC茶聚,帶來的不速之客蘇先生我一眼就認出來,三十年不見一點都沒有變。
那天喝完茶,不想立即回家工作,乘自動扶手電梯上到荷李活道閒逛,經過文武廟,本打算兜去曾經住過兩晚的普慶坊看看,方向一時搞不清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順腳進了廟宇參觀。論古雅精緻,自然不若台南那些景點,但裊裊煙火肅穆得來十分家常,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樣感到寧神。大殿偏廳依次遊過,不知怎的,那次和A在巴黎聖母院的一幕浮了上來:一進門有個理事的神職人員大喝一聲,命令他脫掉帽子。語氣非常兇惡,完全沒有通融餘地,指責的雖然不是我,也窘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那時他已經發過幾次病,體質很弱了,長途跋涉由美國飛到歐洲,疲累不在話下,脫了頭頂保暖的配件,不小心冷傷風怎麼辦?
人死後一了百了是最大的安慰,一切化為烏有,塵歸塵土歸土。但基於自私,有時我倒願意相信輪迴,假如他投胎再世為人,今年二十三四歲,還可以轟轟烈烈再談一場戀愛。我保證,這次我會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