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呂永佳善於寫詩,也自言偏愛詩,但他兼寫散文,因為散文「夠真」,他說:「讀散文如見人。作者的人格在散文中浮現出來,這也是散文的危險,你始終逃不過精明的讀者。」在他剛交出的最新散文集《於是送你透明雨衣》中,從教育省思、感情關係,到童年回憶與親情等,都是他創作中常見的主題。
反覆往來,舊事重提,呂永佳說自己寫的,從來都是生活。
他認為,文學不是篤信,是梳理,「它會不斷反覆挑戰、反駁你自己。你不透過寫作這個動作,可能會懵懵懂懂,朦朧的,但寫出來會慢慢還原,像撥開霧,看到自己的模樣。」
〈舊事重提〉,是魯迅散文集《朝花夕拾》於雜誌發表時的文章總題。這是呂永佳最喜歡的散文集。朱少璋在新書序言中,寫道:「說『舊事重提』,是典型的散文筆法;說『朝花夕拾』,就滿有詩歌的比興意象。」呂永佳也是在朝花夕拾。從二○○九年第一本散文集《午後公園》,來到逾二十年後的第三本散文集,來來回回在他筆下依舊是寫公園、屋邨、童年記憶、家庭親情。他說:「對散文,我始終有個執着,把我生活上貼地的、很真的感受,忠於自己地寫出來。」

呂永佳最近出版第三本散文集《於是送你透明雨衣》,由匯智出版,收錄五年間創作的散文。
⚡ 文章目錄
不是還原回憶, 而是書寫現在
在他撿拾過去時,即使同一個公園,同一段少年時光,相距廿載,還是有心境上的轉換。「有些讀者說沒有轉變,覺得是相同題材;有些看到我再寫家庭時,牽涉到生死訣別的要素,因為這些事貼近了,生活思考也多了。有些東西會永遠失去,倒過來說,永遠得到又代表什麼?像回憶永遠在腦內,它是什麼呢?」他認為,這種永遠縈繞不斷的,就是需要不斷詮釋的東西。「一段回憶,在今日令你很舒服,明天可能令你很痛苦,都說不定的。我不是還原那段記憶,而是我今天如何看那段記憶,它如何反射一些東西給我。」
他指,自己多年來書寫家庭,都是重複一個動作:往過去的時空投擲一些東西,期待有另一些東西反彈回來,帶給今日的自己。例如他寫父親,寫其為人性格,也憶記與父親的點滴,如昔日考完高考後父親叫他見暑期工,在選科時父親對他的支持等等。如今呂永佳也將近四十,再寫少年成長心路歷程,他認為是詮釋不同片段在生命扮演的角色,像他對社會和人性的看法原來承襲自父親。「我不覺得是回望,而是詮釋。借這個解釋去講我對生命的新看法。我有天都忽然想,我會不會沒有呢,我童年片段都差不多,哈哈,不知再往哪挖。不過愈寫,都還有東西可寫。原因可能就是,我不是寫童年回憶,而是寫現在。」
他甚至反問:為何不能回首過去?「我覺得過去、現在、未來,不是如此簡單分成三段,而是不斷交叉,亂晒籠。你梳理它,可能就是寫散文。」公園經常出現在他的作品裏,他坦言,以前單純寫公園是懷念時光,現在書寫則滲雜很多失落。「像荔園拆了,有沒有另一個荔園?再重建,我再去寫也不一樣的。或者現在我覺得公園已經不能給香港小朋友同樣的感覺。那個空間已經不同了,不會在我生命中再次出現。這些思考在我二、三十歲不會這麼多。生活到了不同階段,是有不同的尺去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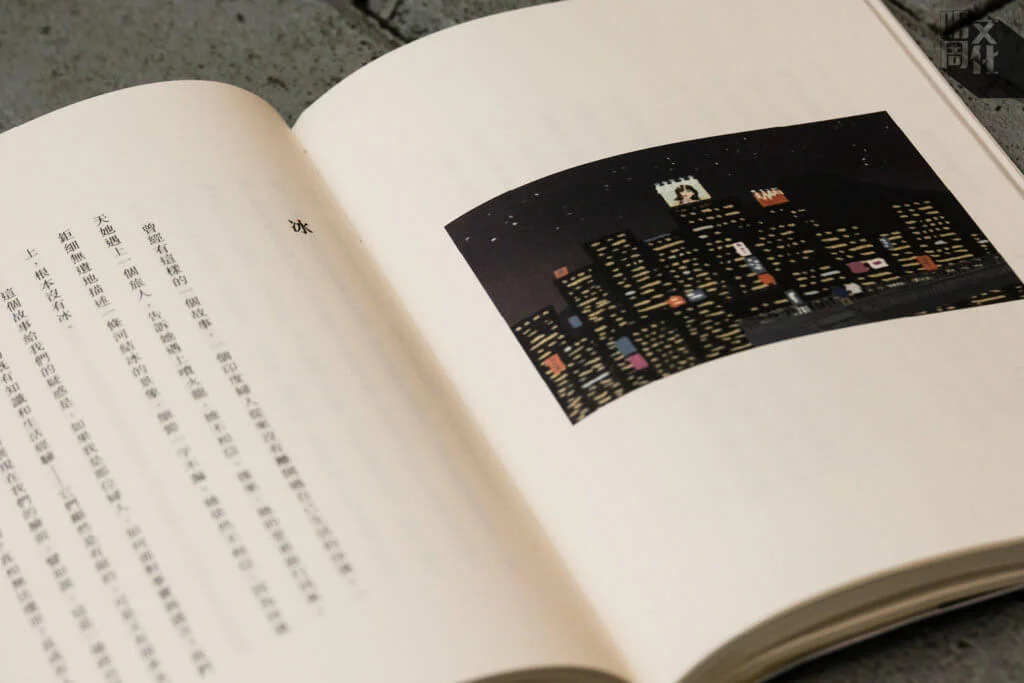
作品既書寫成長心路歷程、感情的細軟感受,也有對教育的反思。
當世界要你努力去考取功名
除了親情和愛情,個人隨想,現職教師的呂永佳,也寫了不少對教育的反思。有時他會在學校寫作,興之所至便會書寫,有的是對高層的批判,也有對老師自身的反省。他在書中反思,老師最大的錯失是想學生走自己走過的路;他頓悟老師只是普通人,實際上比學生更軟弱,比常人更迂腐;他甚至直白寫道——「很多時,教師正是生活的失敗者,卻要站在講台上,裝起成功的模樣。」
呂永佳任教職十餘年,他覺得,老師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無論是道德或知識上都能教導他人,但他自覺都是普通人,反之對學生的同情較多。他說的這份「同情」,不是來自高位的同情,而是自覺比較幸運。「他們生活的時代比我們更多挑戰,而且很多事他們不能控制。當有學童自殺,我也不是批判。我在學生的身上反而學到很多,譬如初心、善良、簡單,是我們成人世界沒有的,為了利益或成就而忘記的。很多老師不會再敢去追尋,因為他們到了某些年紀,有其負擔,如家庭和事業,不想粉碎建立了的東西,某程度可能他們本性是好,但這方面是失敗了。」
他不諱言老師這個身份的失敗,在於說一些連自己都不信、但社會信奉的說話,「很多人是沒有反省。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迎合或捍衞了一些觀念,像讀大學就是成功,很多老師都是這樣想。這是失敗的。」他反覆在書中質問,教育界和社會對於成功與失敗的標籤,從自己的求學歲月,到教職生涯的觀察和經驗,他不斷敲問社會的期許與價值觀,以及教學的本義。「你教到怎樣的學生才算成功?是否5**就等於好,或者level 1就是很差?好簡單地用這把尺去度人,度自己,我也覺得很失敗,用你衡量自己是否成功的方式去告訴學生。有時我自己也是,好自然,因為在那個環境下。」
而呂永佳的履歷表,的確符合他所指的社會「成功」標準。那麼,又會否覺得自己是失敗者?他遲疑片刻,回話:「或者說,我又不會一刀切,是成功或失敗。社會對老師的期望很多,他更要捍衞那個成功的模範,若果我去judge這個成功模範,我覺得老師是失敗。由小到大我們會被灌輸一種你要努力做人的觀念,我自問都是,努力讀書,努力搵工,努力工作,但我們很少去問,這些是否我們想要的。」
散文要真
呂永佳說,依靠寫作的反思自省,剖開了他內心,找到真正的自己,或者是另一個自己。「散文的精神要真,至少要忠於自己的感受。有些可能不能說,但不代表要說假話。」
他借魯迅《朝花夕拾》作自我提醒,「他那些文章寫得很真,是直於面對自己的絕望。這一種我很警覺。」他指,很多老師揚言自己很成功,高談闊論如何教學生才好,他直呼「頂唔順」,不禁反問:「學生真的覺得你好?我討厭自大的人,有些是很自大的老師或作者,會教訓人。」呂永佳正正同時身兼這兩個身份,故此他一直都警覺自己:「像『好心你用心讀書,日後搵工。』的說話,講過無限次,我可否不講?我在散文中是這樣寫,但可能(現實中)我也會這樣做。」
「對於我來說,是真的有掣肘。(散文)那個『真』的地方,就是掣肘。我想做B類人,但我做不到,要被迫做A類人—的這一點真。」或者也是他對自身在成功與失敗之間的思量反省,也許是年近四十的自覺,再次詮釋履痕斑駁的來時路。他在書中如此寫:「如果二十歲是十字路口,以為有很多路可以走,三十歲或許就只是一個沒有出口的迴旋處:循環的疲累。」至於四十歲的啟蒙,他認為是:「不要虧欠你自己。」
PROFILE
呂永佳,生於香港。香港詩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著有詩集《無風帶》、《而我們行走》、《我是象你是鯨魚》;散文
集《午後公園》、《天橋上看風景》。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城市文學獎、李聖華詩獎等。曾任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城市文學獎評判。作品曾被翻譯為英文、韓文、日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