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家賈德(Tony Judt)二〇〇九年確診漸凍症後,與另一歷史學者史奈德(Timothy Snyder)多番會談,回顧二十世紀種種思潮以及個人經歷,對話後來謄錄成書,題為《想想 20 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從章節序列可見,賈德一生身份多變:馬克思主義學者起家,演變成多元論自由主義者;一度信奉猶太復國主義,後來成為批評以色列的美式道德言師;主力研究法國,旁涉中東歐地區史,最後以社會民主主義框架總論歐洲戰後進程。數番華麗轉身,賈德其人其著不無非議,《想想 20 世紀》亦不缺自白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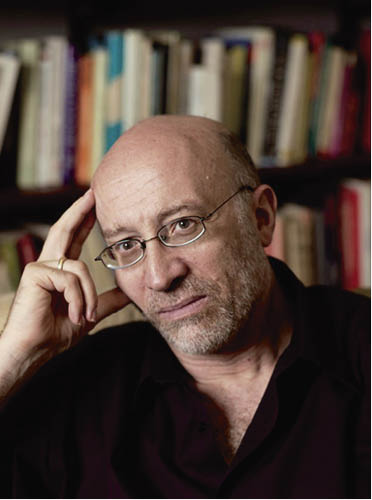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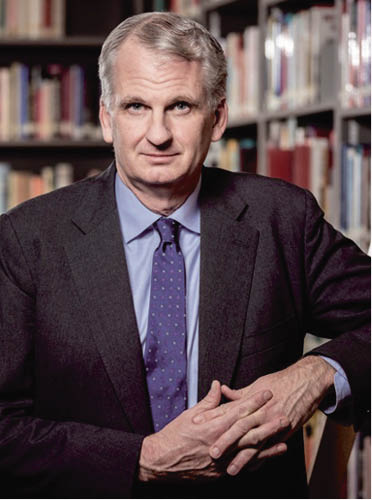
賈德早期專著聚焦法國的左翼政黨史,論點受馬克思主義啟發同時,亦可見其分歧。譬如《普羅旺斯的社會主義》以社會經濟結構—人口以小農和獨立手工業者為主—解釋普羅旺斯地區社會主義政黨的興起,卻以文化因素—支持社會主義政黨變成傳統—歸結當地左翼政黨存續的緣由。據其自述,賈德期望一方面「捍衞甚至實行某種馬克思主義」,同時與之保持距離;後來與之決裂,源於受傅勒和柯拉科夫斯基的觀點影響,認定馬克思主義「無法在政治上實踐或者體現任何道德價值」,同期轉向倫理論述,埋首「月旦人物的思想史」,以泛道德論針砭時人,特別是法國左翼:《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左派》慨嘆眾多左翼不欲參與匡扶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工程」,反而執着於終結資本主義,最終淪為極權共產主義幫兇;《過去未完成》從自由主義出發,仰賴「本質上是概念性甚至是道德性的」論證,狠批沙特和西蒙波娃一眾知識分子擁護蘇聯「愚蠢」「可恥」;《責任的重擔》則借褒揚卡繆、阿宏和布魯姆的道德勇氣—「他們都是反共人士」—反襯法國知識界普遍缺乏「正義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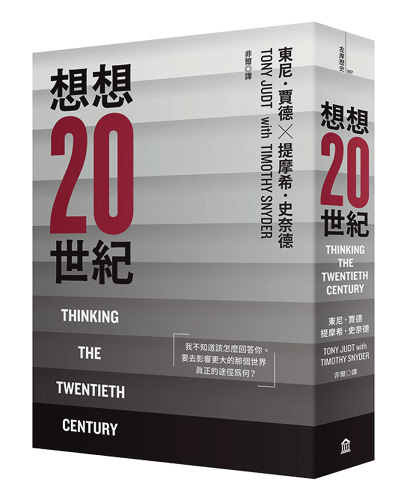
以道德論介入歷史,難免有去歷史化之嫌,淪為政治宣傳,可惜賈德筆下問題不止如此。美國政治學者韋理(Dylan Riley)批評,《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左派》一邊高舉社會民主主義,一邊頌揚密特朗上台將法國左翼光譜「正常化」—然而正是密特朗引入新自由主義瓦解社會民主共識;賈德將沙特打成「自製道德失憶症」的史太林主義者,完全無視沙特長年對史太林的諸多批評,批判極權的德布雷則被斥為極權國師,只因不符自由派框架;《責任的重擔》三位人物其實另有一個共通點:殖民主義者。戰後布魯姆出兵鎮壓越南反殖勢力,卡繆對此保持沉默,又與阿宏一同支持英法以三國入侵埃及奪取蘇彝士運河;而阿宏之所以反對法國捲入阿爾及利亞戰爭,純粹出於「代價過高」。被問到為何不曾譴責法軍暴行,阿宏回答既然無人贊同酷刑,也就毋須特別開口反對。反共宣傳效果有餘,以道德和正義為經緯則欠缺說服力——偏偏賈德認為本書最能代表「我是誰以及所為何事」。
賈德恐怕無法兌現自己對知識分子的期許—「真實不虛」(truthfulness)及「融入情境」(contextualizing)—甚至有違歷史學家的職業倫理:「你不能為了眼前的目的而去捏造或者剝削利用過去。」「匡正某些對過去的錯誤解讀,通常是為了迎合當前的成見」,做法等於「背叛了歷史的目的,也就是要了解過去。」話音剛落,賈德就自認「或許我自己也過度沉迷於像這樣子的練習。」他的例子是《過去未完成》,或者其他著作一樣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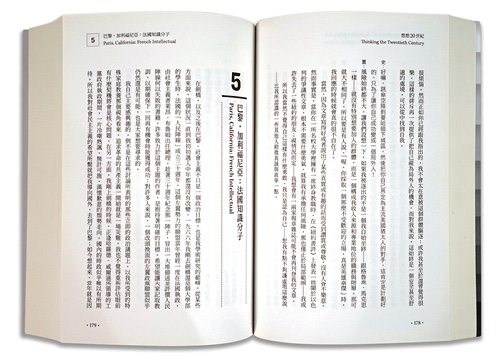
《戰後歐洲六十年》被視為賈德畢生巨著,然而書中未發新論,亦無考掘原始史料,賈德解釋本書旨在涵括文化藝術,以及引導讀者將六十年代想成「社會民主的時刻」。賈德念茲在茲社會民主政體,視之為唯一出路,然而從未分析由七十年代起陸續觸礁的福利國家如何回應當今世界,尤其是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的全球化時代,究竟是否適合凱因斯式擴大消費以振興經濟。如果說西歐模式的經濟計劃相當於「在為了投資長期基礎設施所需的已知科技和擺平消費者不滿的即時政治願望之間所達成的妥協」,環球資本霸權底下,單一國家愈來愈難控制資本,福利政策隨財政自主權同受壓縮,妥協空間已經所剩無幾,遑論更有歐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一類組織推波助瀾。時鐘停擺在戰後三十年,無助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懷抱政治目的修正歷史,理由可以冠冕堂皇。賈德指出歷史學者有兩大責任:一、「釐清某一個特定的事件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二、身為國家公民「有責任運用我們之所長去服務於公眾利益」。著述時後者壓倒前者,立意再好,充其量是個良善的平庸史家。

作者簡介
陳國榮,半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