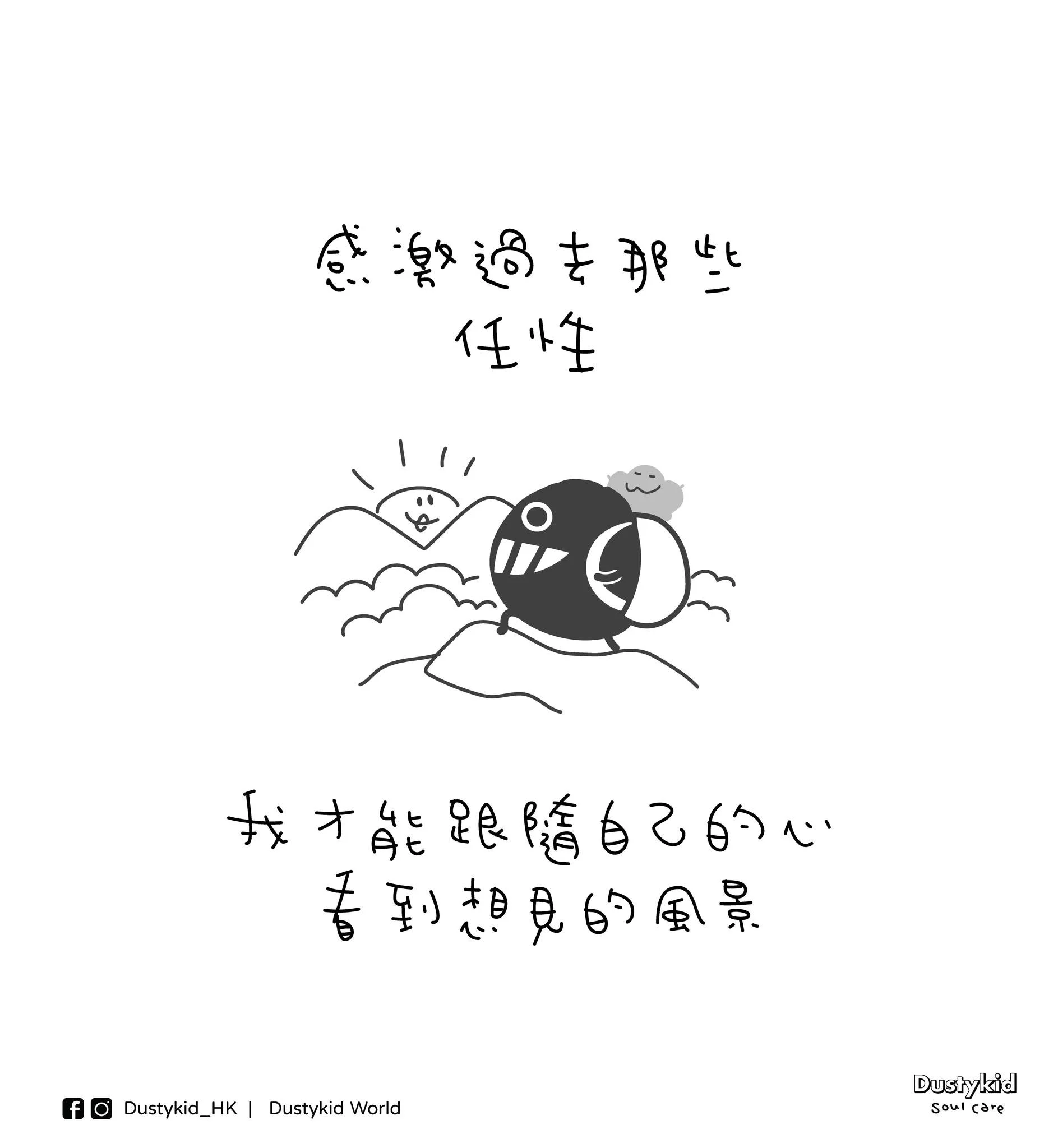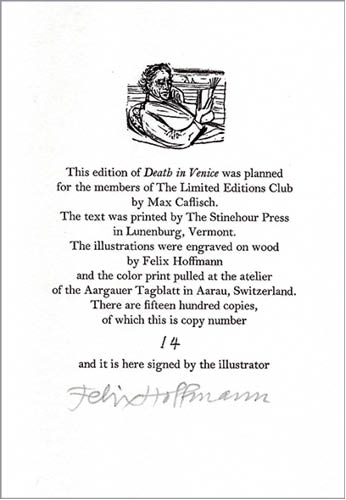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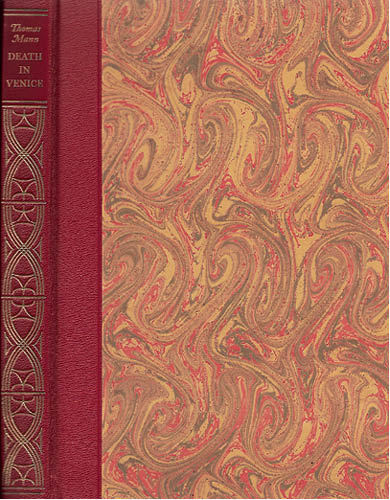
⚡ 文章目錄
尋藉口請來死亡
人皆有死。但是不能以此為放任的藉口。在瘟疫肆虐的日子裏,照樣有年輕人在沙灘開狂歡派對。如果有好管閒事的上前問着他們,他們會回道:「有什麼好怕的?死麼?人橫竪遲早都是一死,不如行樂及時。」照我以往的經驗,這類人往往正是最為怕死的一族,但是偏偏打着死亡的旗幟自我放縱。奇怪的是死亡原來也可以用來做藉口。目前大家依舊活在瘟疫的陰影之下,一般都只是安分守法地自求平安多福,但是也有人趁火打劫,從中取得利益。這樣一來,瘟疫就成了個題目或幌子。瘟疫能有多重的象徵意義。有人認為它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和懲罰;人類大肆破壞傷害地球,地球終於發出嚴正的警告了。它更可以象徵混亂、罪惡、死亡。有關瘟疫的小說繁多,隨便想起的就有笛福的《瘟疫年的日記》,加謬的《瘟疫》,加西亞馬蓋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但是我卻忽然想到了德國小說家湯馬斯曼 ( Thomas Mann, 1875–1955 )的《死在威尼斯》( Der Tod in Venedig, 1922 年初版)。這個中篇小說裏面也描述了一場瘟疫。
維納斯浮升海上
小說中的主人翁是一位有名譽地位的作家吉斯托夫.凡.艾森柏。艾森柏年過五十,鰥居,無子,生活克己,專心創作。一天他出外散步,在墳場附近遇到了一個仰鼻露齒相貌奇醜而又兇惡的陌生人。這場偶遇叫艾森柏心緒不寧,興起了旅遊的渴望,於是決定前往威尼斯度假休息一段時間。在途中船上他又遇到了一個化了濃妝的老年男士,和一班年輕人在一起嬉戲玩耍。到了威尼斯的大酒店之後,他在那裏遇見了一名年約十四五歲的波蘭美少年,名曰泰佐。艾森柏情不自禁迷戀上泰佐,不能自拔。真正是千年道行一朝喪。他一生信奉的是完美冷靜理智的藝術創作,如今這美少年卻叫他苦心經營的藝術世界如同紙牌屋一般立即瓦解。苦心經營出來的所謂「美」是虛假的,沒有生命。美渾然天成,不費吹灰之力。美一下子就出現了:愛神維納斯踏着貝殼浮升海上,金髮飄飄。就是那樣。後來艾森柏發現威尼斯出現了霍亂疫情,但是威尼斯當局以及酒店旅遊業偕聯手隱瞞。有些比較機警的旅客已經陸續離開,但是泰佐一家人卻依舊留在威尼斯,彷彿懵然不知疫情。艾森柏本來打算冒昧相告,卻又打消了這念頭。因為他不願意失去泰佐。艾森柏漸漸失魂落魄,在運河橋邊,或聖馬可廣場,到處尋找泰佐的蹤影。後來還不惜上理髮店染髮化妝,企圖藉此取悅泰佐。艾森柏最後一次看到泰佐是在海灘。那時候他已經感染了霍亂而不自知。艾森柏獨自坐在沙灘帳篷前面,看着泰佐走向遠方的海洋。但見泰佐舉手,彷彿遙遙地向艾森柏招喚。艾森柏努力回應,結果卻頹然倒下,一命嗚呼。這裏的海洋代表無限,代表艾森柏追求的完美,但在這片完美之中出現了代表情慾的泰佐,摧毀了他的世界。
美少年引入冥界
《死在威尼斯》最妙之處是神話與現實的混合。「這就是威尼斯,這賣弄風情,形迹可疑的美麗城市,半是童話仙境,半是遊客陷阱。」作者在描述美麗的聖馬可廣場之餘,不忘提醒讀者運河的河水發出異味。艾森柏一路上遇到的幾個人物,像墳場的陌生人,船上的老來嬌,貢多拉船夫,以及後來在酒店花園賣唱的歌手,都大同小異地仰鼻露齒大喉結,其實都是死神的化身罷了,一再向艾森柏預示他的結局。當然,最後連他迷戀的泰佐也只不過是引領他進入冥界的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Hermes)。
藝術家走向瘋狂
作者筆下的泰佐亦是神話與現實的混合。作者一力描繪泰佐那如同花朵一般的模樣,高雅優美的氣質,一再將他比作希臘雕像和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但有一次艾森柏在電梯和泰佐相遇,近距離觀察他,發現他的牙齒發黃而欠缺健康,想到或許泰佐不會活得太長久,竟然暗自竊喜。在這裏作者亦捕捉了人性陰暗的一面。漸漸地艾森柏發覺威尼斯的大街小巷到處有消毒藥水的異味,叫人聯想到腐敗和死亡。他向酒店經理及侍應探問,他們都是支吾以對,含糊其詞。最後還是一位比較老實的旅遊經紀向他透露瘟疫實情。他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覺得滿足得意。為什麼?可能是他自己的世界因情慾而傾倒,他很高興看到這客觀的世界也因瘟疫而遭到破壞。因為情慾,如同罪惡,並不適宜井井有條的日常生活。情慾喜歡社會的秩序鬆懈,喜歡世界混亂,因為這一切使情慾有機可乘,趁亂得其所哉。艾森柏甚至願意和威尼斯一同隱瞞疫情。威尼斯為的是旅遊事業的利益,艾森柏為的是他的私人情慾。
值得注意的是在湯馬斯曼的另外一個中篇小說《東尼奧.克略格》(Tonio Kröger, 1901年)裏面,將藝術家比作罪犯流浪漢那一路的社會邊緣人物。作為一個小說藝術的創作者,時常游移於理性和感性之間,既想追求完美對稱,又想捕捉情慾的歡樂瘋狂。但這情慾又可以如同瘟疫一般摧毀藝術,導致藝術家的沉淪。藝術的完美和清醒既得之不易,復又易碎,藝術創作如走鋼繩,能不慎之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