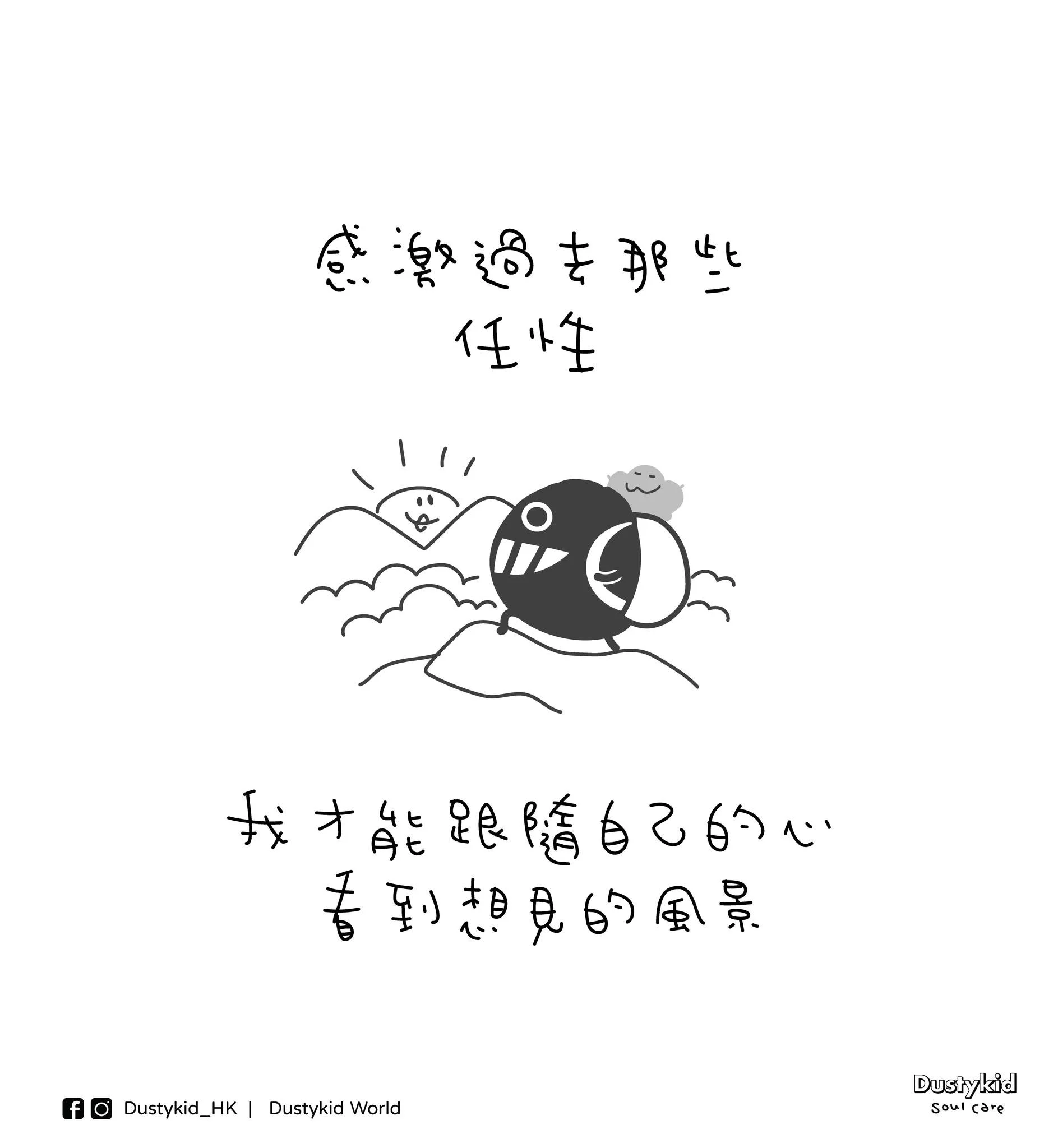後來應該還來過的,但沒有任何印象,第一次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也並非因為是第一次,而是因為用餐時手舞足蹈,樂極生悲不小心打翻一杯紅酒,弄髒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彷彿聽人說過,清除布料上紅酒迹的最佳辦法,是狠狠倒白酒上去,立即有負負得正的神奇效果,我當然缺乏表演魔術的勇氣,匆匆跑進洗手間胡亂用水沖沖就算數。大概不足以構成災難──那些年一天到晚穿黑色,潑什麼上去都沒有顯著污痕。
飯後還若無其事到對面的同志夜店Palace跳舞。那次是招呼紐約朋友K,身高六呎四吋的他所向披靡,不論在任何地方出現都成為焦點,我們一進場,就被矮他兩個頭的亞男盯上,一如所料神女有心襄王無意,夏夜蚊子一樣圍在身邊飛來飛去,殷勤盡獻徒勞無功。臨走死心不息,塞過去寫着電話號碼的小字條,K禮貌收下,待人家一轉頭就扔掉了。故事竟然有餘韻:幾年後畫家張先生大排筵席,座上客駭然包括這位吃不到天鵝肉的蚊子,幸好他完全不認得我,我也提都沒提。
這次也是款待遠方來客。訂了票看演出,小劇場在附近,否則根本不會考慮光顧,每冊旅遊指南都有它的地址,自命高貴的導遊覺得交行貨有損聲譽。既來之則安之,簡略介紹悠久歷史免不了,當然不忘指出從前熟客放餐巾的木抽屜,像老式藥材鋪藥箱,名字寫得一清二楚,包管甲昨天留下的油漬今天不會擦在乙的唇邊。如此不衞生的規矩,一早已經廢除,有趣的是保留了點菜時侍者把客人選擇寫在餐枱紙的習慣,結賬伏低身加加減減,龍飛鳳舞筆劃潦草,他說總數是多少就是多少,無從得知有沒有計錯數。
店號定位既不是bistro也不是brasserie,而是更冷門的bouillon,今時今日市內幾乎絕無僅有。直譯「清湯」,教人想起英美救濟窮人的飯堂soup kitchen,可見出身之寒微。不學無術的我熟悉這個字,都拜初來巴黎時一個常看的電視節目《Bouillon de culture》所賜,這碗《文化湯》一星期一劑,主播是鼎鼎大名的Bernard Pivot,此人不但在法國家喻戶曉,被奉為讀書界指南針,國際聲望也很高,名字連不諳法文的知識份子亦耳熟能詳,剛剛認識小思老師,她就馬上問我有沒有定期收看。全盛期主持的《Apostrophes》據說非常益智,可惜我來得太遲,《文化湯》卻有種倚老賣老的江湖味,向來不屑聽權威訓話的超齡反叛青年只覺聞名不如見面。有一輯以中國作者為主題,尤其慘不忍睹,人名唸得五音不全,隨隨便便打開譯本讀幾句敷衍交差,我一面看一面罵,男友的民族自尊被冒犯了,黑口黑面說道:「吵什麼吵,不喜歡看就不要看!」
另一個文化節目主播叫Bernard Rapp,名氣沒有老行尊大,態度誠懇得多。這個賓納後來轉行當電影導演,拍了沒有兩部就去世了,才六十出頭。Jean-Luc Delarue死得更年輕,那時他被捧為明日之星,鋒頭十分勁,緋聞經常登上八卦周刊,有一張照片穿件白色浴袍,整個胸都是濃毛,平日根本看不出。走紅後醜聞一宗接一宗,神神化化機艙鬧事,被揭發酗酒之外濫藥成癮,電視台即席炒魷。聽到死訊嚇一跳,因為不知道他生病,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後期的照片老見他瑟瑟縮縮穿厚大衣戴冷帽,又矮又瘦,比意氣風發時細了至少兩碼。
我最喜歡的是主持深宵音樂節目《Taratata》的Nagui,原籍埃及,皮膚偏棕,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巴,令人禁不住幻想渾身上下無一不大。微微沙啞的嗓子性感極了,英語講得噼嚦啪嘞,訪問英美歌手一腳踢即場翻譯,並且不忘調情說笑,迄今無人能出其右。還有一個不定期的Frédéric Mitterrand,是米特朗總統的侄兒,明星特輯做得深入淺出,資料齊全含情脈脈,完全痴心影迷格局,簽名式的「晚安」鼻音濃濁,傳為一時笑柄。
奇怪,我一直標榜自己不看電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