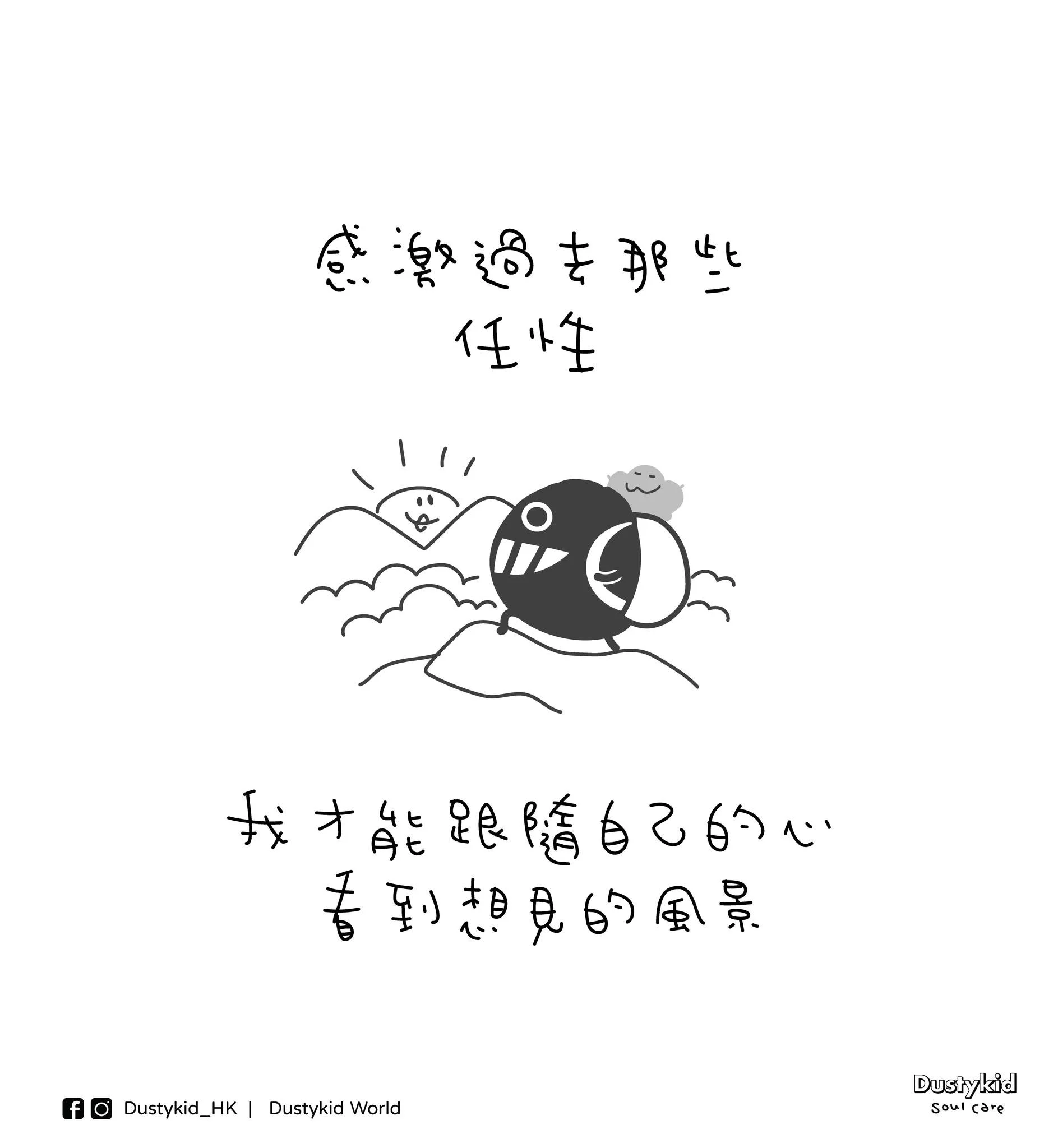對不必上班的人來講,星期一沒有催生頭痛的特異功能,因為天天游手好閒,別人投訴兩日風流換回來一整個早晨的折墮,實在匪夷所思。不無一點希望博得同情的誇張吧?除非真的四十八小時馬不停蹄作樂,眼睛沒有閤上過,但要真是那樣,只能說活該。
街角老婦人大概聽也沒有聽過小資的喟嘆,下雨的緣故,上身披了一塊防水的黑色塑膠,下身披了另一塊,非常漠然地進行她的工作。我有點懷疑服飾靈感來自她天天接觸的垃圾袋,效果出奇地時尚,日本叱咤風雲的某某和某某,費盡心思舞動剪刀,追求的境界也不外如是。頭上的帽子則教人想起水上人家,遮住了大半邊臉,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防曬,但在這個拖得太長的亞熱帶冬季,擋風擋雨竟也一樣適宜。
莫名其妙想起小時候大人教的一首童謠:
落大雨,水浸街
阿媽擔柴上街賣
坦白說,當時很討厭土裏土氣的歌詞,覺得我母親的形象徹底被侮辱了。舉止斯文的她,和擔柴這種粗重工夫風馬牛不相及,擔上街還要高聲叫賣,銅鑼般的嗓音響遍窮鄉僻壤,簡直受不了。長大後我們的關係傾於疏離,用文明的說法,是保持距離互相尊重,但和所有正常的小孩一樣,我曾經對她有份原始的偏袒,甚至朦朦朧朧的崇拜。唸小學二三年級,有一天幾個同學竊竊私語,說我媽媽從前當花旦,「做戲子」當然不是抬舉,喜歡看戲的我卻禁不住一陣虛榮,深深惋惜事實並非如此──無話不談的鄧姓朋友推測那是因為衣着打扮太過潔淨,與大部份粗枝大葉的家長截然不同,「他們也這麼說我媽媽,尤其是那次見過她穿旗袍。」許多年後坐在冷氣勁放的皇室堡戲院看《花樣年華》,尷尬地笑了。
別誤會,我並沒有故意把惱人歌詞藏在記憶庫,有事沒事翻出來享受自我折磨的樂趣,它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偷渡入境及居留,而且練成隱身術,平日根本無跡可尋,只在興起的時候出其不意躍到跟前嚇人。這次住在中環一棟公寓,電梯循環錄音帶裏的歌就是好例子,由地面到十五樓所需不過一分數秒,出出入入總要受「噢你也在這裏嗎」的刺激。相遇最頻密的一首叫《午夜在綠州》,剛到三藩市常常在無線電聽到,後來認識A,他唱片架駭然有Maria Muldaur這張黑膠,作暈眩狀之後加贈無聲尖叫。中東獵奇色彩的歌詞實在爛:
午夜在綠州
把你的駱駝遣上床
影子繪在我們臉上
絲絲羅曼蒂克在我們腦裏
媽媽咪呀,甘廼迪總統的名言一點沒有講錯,勿問亂七八糟的歌詞能為你做些什麼,只問你能為亂七八糟的歌詞做些什麼。另外是《A Time for Us》,歌手認不出──來自電影《殉情記》,原本有音無字,影片賣個滿堂紅,主題曲填上庸俗且空洞的詞,居然大受歡迎,一時之間男唱女也唱,莎士比亞要是得悉羅密歐與朱麗葉隔了幾個世紀以這樣的姿態飛入尋常百姓家,一定啼笑皆非。還是原名《四二年夏天》的《初渡玉門關》乾淨俐落,不填詞在大氣波赤裸裸熱播音樂,幾十年後流落在升降機裏,昔日顧曲周郎毫無困難就認得。
《我們才剛剛開始》播的是木匠樂隊版本,主唱的嘉倫那把聲音我一聽就有吞口水衝動,她年紀輕輕死於厭食症,滋潤喉嚨下意識有驅趕恐懼作用。他們兩兄妹長相實在薯,編曲呆板乏味,迎合的是避過嬉皮士洗禮的小乖乖,主流電台奉為寵兒。應景的《下雨天和星期一》雖然沒有收在電梯循環錄音,仍然不請自來:
吊兒郎當
除了皺眉沒什麼可做
下雨天和星期一往往令我情緒低落
不知怎的,我想起數天前電車見到的一個老男人,肩上披着一塊春花朵朵的毛毯,逕自坐在那裏發放喜氣。近年大都會患抑鬱症的人似乎越來越多,我一直認為那是選擇性疾病,你不讓它來,它沒有辦法來。